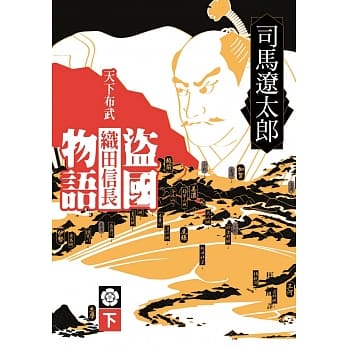具体描述
若真是才学惊人,又何苦要入赘?
一个现代的超级金融大亨,被最好的朋友背叛,然后他就死掉了。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就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古代的赘婿,姓宁,名毅,字立恒。
赘婿,也就是娶老婆之后住进岳父岳母家的男人。
在那个年代,赘婿的社会地位极低,比普通人家的小妾还低,活着的时候祭不了祖死后也进不了祠堂,就连生下来的孩子都得跟着老婆姓。
上辈子阅尽繁华、历尽沧桑,如今能有机会重新开始一段悠闲的古代生活,似乎也不错?没地位就没地位吧……
于是他每天写写歪诗、唱唱饶舌,晃晃荡荡当个闲散姑爷,过得挺舒适。
可惜人非草木,谁能无情?
当身边亲近的人们遇到了天崩地裂的大麻烦,他又怎么能够视若无睹?
于是上辈子曾经叱咤风云的宁毅,也只好缓缓走到幕前,吟出了他的开场白:
「你们这些人,过分了……搞得入赘的也不得安宁哪……」
本书特色
A.超好看的仙草等级的架空的穿越的历史的长篇的小说
B.中国最大小说网站「起点中文网」历史类点击排名第2推荐排名第10的小说
C.1800万读者读过300万读者推荐的小说
D.极简风包装又带着淡淡的典雅与华丽值得收藏后再三阅读的小说
E.使用贵松松高级水彩纸+镂空书衣出版社完全入不敷出的小说
F.使用《清明上河图》作为封面到时候可以拼成一整幅挂到墙上当成传家宝的小说
G.随书附赠方便实际耐用有趣的「微型版赘婿封面书签」让你走到哪看到哪的小说
H.以上皆是
著者信息
愤怒的香蕉
本名曾登科,男,湖南长沙人,刚满而立之年的金牛座。
擅长生活和感情描写,笔风细腻温馨,作品有独特的见解和浓厚的个人风格。
他的每部作品均受读者喜爱,是一位慢工(此处应有嘘声)出细活的精品型作者。
着有《隐杀》、《异化》,《赘婿》连载中。
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三十岁生日随笔:海洋
今天我三十岁。(编按:此文撰写于二○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照例,每年的生日写一篇随笔。而立之年,该写点什么直到今天上午都还没什么概念,不是无话可写,而是可写的太多了。
不久前我跟人说,人在十岁的时候看自己,你是十岁时的自己,二十岁的时候看自己,你是二十岁的自己,到了三十再看自己,你会发现,十岁、二十岁、三十岁的自己都站在一起了,留下了那样多的痕迹,分也分不开。
所以我有三十年的事情可以写。
往日,我会尽量写点轻松的,或者是务实的、不难理解的,后来想想今天的开端,来写点形而上、假大空的吧。
说三个概念——或许合併起来便是大部分的我,期间有些古怪的中二的东西,看下去,该会理解其原因。
一,文笔。
二○一四年年底,我去北京鲁迅文学院参加了两个月的课程,其中有一节课是北大的戴锦华教授讲的,她提到一个概念:在文字的源起过程里,中国的文字是表意的,欧洲的文字是表声的,这是两者最大的差异。
戴锦华老师在北大研究的并非语言,而是电影、大众传媒等方向,提到这个概念,是因为内容稍稍触及,随意提过去而已。这个概念,我从前是听说过的,讲课结束后便举手提问了,问题大概是:文字存在的基本意义是传递思维,也就是将脑子里的无形思绪具现化,传递给他人,使他人得以接收;在《三体》和很多科幻作品里,也曾描述过类似蚂蚁那样、整个族群由一个母体统治的族群,并且认为那是生物进化到高点的一个途径。东方的文字以图形表达意思,西方文字先将意思化为音节,再通过一套约定俗成的方法做译解,这样是不是多了一道工序?这两种发展的分歧有没有什么客观因素和发展的必然性?
这个问题其实问得有些乱来,因为与戴教授的课程内容无关,只是在边角料上挑了一个话题做引申。戴教授当时愣了一下,然后说:「这可能没什么必然性。」
我问:「可能只是意外导致的差别?」
她说:「嗯。」
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有了很多想法,在这里先不讨论——我之所以说出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重要,以至于我随时随地都放在脑子里转。
语言文字对我来说,最具魅力的一项,便是思维的传递。
我三十岁,高中毕业,写网路小说,至今也算不上真正的被社会所肯定——当然,我去鲁院学习过,参加过几个不大不小的会议,我没有加入作家协会,我的成绩也只是在小范围内不上不下的,但如果你一本正经的问我:「你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我可能会回答:「我做传递,思维的传递。」
《圣经‧旧约‧创世纪》里有个神话,我一直很喜欢。
在古代,因为人类没有语言隔阂,所以无比强大,同心协力建造了巴别塔,试图夺取神的权威。神没有毁灭人类,只是让所有人开始讲不同的语言,然后人类陷入互相猜忌和战争中,再也没有能够团结起来,巴别塔因此倒塌。
这真是无比简单又无比深刻的哲理,人类的一切分歧和问题,几乎都来自于彼此思维的不透明。我在二十七岁的随笔里写过野猪和道德的关系(编按:载于第一部第六集),欺骗来源于利益,但也由此诞生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所有的喜剧悲剧,所有的规则现状。
语言文字是补完人类的最重要途径,它用于传递想法、意图,承载智慧,无论是对科学的认知还是对人生的感悟,我们都可以通过文字进行积累,传递给后人,让他们迅速成长,而未必需要一件件的去试验或经历,由此,当他们遇到同样的问题,便能做出更好的选择,拥有更好的人生,人类社会也此获得进化……
我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第一次在村上春树的书里接触到「文字具有极限,不可能表达全部的思维」这个概念,之后几乎像是豁然开朗,此后十年,我孜孜不倦的思考如何将思维转化为尽量准确的文字,我丢掉那些华丽的连我自己都不明白的不必要的笔调,留下简单的枝条,再将叶片变得繁盛,再进行修剪,如此一次次的轮回,到如今三十岁了,我仍旧继续修剪着这种笔调。
有人觉得我的文笔不错,有人不然。当然各有其理由。
二,性格。
我的性格存在着极大的缺陷。
这样的性格缺陷源于接受教育时经历了错误的顺序、进行了错误的构架。启蒙的时候,爷爷教给我的是非常正确正直的思维方式,后来我读鲁迅,常常在作文上模仿鲁迅的笔调写东西,我的文笔不好,老师说我想法也不好,对此我很疑惑:我在抨击坏事,为什么想法不好的反而是我呢?想通之后,这便是最初的分歧和格格不入——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经历了这些。
接下来我经历的是一个急速变革的年代,曾经有一个读者说我见证过当初那个时代的余晖——确实如此,那个变革尚不剧烈的时代的余晖,之后便是剧烈的变化,各种观念的冲击,自己建立的世界观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了。再然后,由于家庭的困境,我放弃了大学,至此,知识在我脑海里也不再拥有重量,于是也就没有敬畏,我随意的拆解一切,让所有正统知识都失去了意义。
我时常跟人说,所谓「意义」,来源于「仪式感」,我们小时候玩家家酒,大家都很一本正经的商量碗筷怎么摆、人怎么就坐、餵饭怎么餵,我们清明节扫墓,怎么跪,磕几次头——对于纯粹的唯物论者来说,这些跟鬼神无关,只跟我们自己有关,当我们一本正经的这样做了以后,便会产生「意义」的重量。
最简单的解释是:当我们为一件事情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我们会说服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所以后来,有些不想唸书的书友跑来问我要不要继续学业的时候,我都会劝他们继续,不全是为了知识,更多的是为了在进入社会的时候感受到自己曾经的付出,感受到那种沉甸甸的东西,然后告诉自己: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进入了社会,然后我失去了一切敬畏,我认为所有东西都是可以用基本逻辑解构的,而我的脑子也还好用,当我遇上一件事情,我的脑子会自动回到几千年前甚至几万年前,从原始社会构筑逻辑,一环一环的推到现在,寻找这件事情的所有成因,若能找到原因,脑子里就能产生满足感,一如我在三年前说的野猪与道德。
有一段时间,我怀疑自己可能有着某种叫做亚斯伯格综合症的精神病(编按:对,柯文哲的那个亚斯伯格综合症),这种人以逻辑来构筑感性思维,在我最不擅长与人交流的一段时间里,我甚至试图以逻辑来建构一套跟人说话的准则……
毫无疑问,我尝到了苦果。
若只是存在上面的几个问题,或许我还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的写东西。半年以前我看见一句话:一个出色的作者最重要的素质是敏感,对于一些事情,别人还没感到痛,他们已经痛得不行了,想要忍受痛苦,他们不得不幽默……
我常跟人说我毫无文学天赋,但我确实具备了敏感的素质。
我有时候看我们八○后的人,走入社会之后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改变自己的三观、扭曲自己的精神,在挣扎里,没有人知道这些有什么不妥,直到某一天,大部分人将金钱权利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视为成功的准则,不断的追求,始终觉得不满足,总觉得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开始怀念曾经的青春年少,导致了一大批《匆匆那年》(註一)的流行,但回过头来,纵然金钱权力无法满足自己,也只得继续追求下去……
有些唱高调的感觉,对不对?
有时候在试图解构自己的时候解构整个人类族群,放在整个地球甚至宇宙的时间线上,我看见风沙卷起,一个偶然的瞬间画出了漂亮的图案,人类产生了所谓的智慧,适应世界,改变世界,最后毁灭世界;人类终将灭亡,找不到永恆存在的意义……
这里则显得中二,对不对?
若是我在十八岁的时候想到这些,那时三观尚未完整,还是一些可以改变的中二想法;但我三十岁的时候再回到这个问题上,那就是动真格的了。
这段东西,可能是关于终极的虚无主义命题,我其实不太想跟人探讨——普通情况下它中二度爆表、羞耻度爆表,提一下,也是为了说说第三点。
三,网路文学。
写网路文学很多年,虽然在鲁院的时候,我坚持文学并无传统和网路的区分,但事实上是有的,有人称之为传统文学和通俗文学,有的称之为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我们姑且认为有这样的分割。
我写书很认真,至今我也敢跟任何人理直气壮的这样说,曾经有过作家的梦想——至今也有,只是对于作家的定义已经不同了。
两天前,湖南省召开了据说五年一次但这次隔了十年才办的第六次青年作家大会,我以网路文学代表的身分过去参加,碰巧湖南经视的记者採访,当时也没什么腹稿和准备,说到网路文学的时候,我说,如今的网路文学或许不是文学的未来,但它的中间,包含了眼下走入困境的传统文学所缺失的最重要的一环:吸引力、说服力。
我以前定义文学,通常是这样说:传统文学侧重的是对自我的挖掘和思辨,网路文学侧重的是传递和交流。
在这个定义里,传统文学深挖自我,其挖掘深度决定了文学高度——即使有很多人看不懂,只有思想境界高的人能够看出来,他们在好几层楼这么高的地方进行交流——我并不认为他们没有价值,恰恰相反,这些思想是人类发展中最为闪耀的珍宝,我心悦诚服。
而网路文学,更在乎的是如何将作者脑子里的东西传到读者的心里去。在网路文学发展的这些年里,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手法,当然,有好的有不好的,有良性的有不良的,毕竟还是个良莠不齐的学科。
在鲁院的时候,有一天,我跟一位老师在路上遇见,聊起关于分歧的话题。对方是个很好的老师,但对于网路文学不甚了解。我当时说:「我见过很多作者,他们赚不到钱,为生活所迫,一头钻进最极端的一个方向上,将他们原本的思辨全都放弃了。人都是会这样走极端的。」
对方说:「但也有很多作者,在这个不断下滑的社会风气里坚守着,他们尽力的抵御社会风气的影响,他们的那些思辨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不能没有……」
我当时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十几亿人的精神文明下滑,难道整个文学圈说一句「尽力」就可以交代过去了吗?难道光是独善其身,就算是做到了该做的事情吗?
天,文学可是精神文明的发端哪!
但我没敢说出口。
前天的採访里,记者问:最好的文学是什么?
我说:最好的文学能让人的精神真的得以圆融,当作者说「生活里不该只有钱和权」,人们会真正的相信;最好的文学拥有最大的说服力,它寓教于乐,感染大众,而不是说完以后纯粹让人觉得在唱高调,它能为一个人重塑三观,能将前人的经验真正的留给后人……
不过我当时没有说得这么有条理,恐怕新闻上也看不到吧。
科技将不断发展,其中有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区别,理论科学站在顶点,它赚不到太多钱,但可以得诺贝尔奖;当理论科学取得突破,应用科学——也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便会随着衍生出来。
精神文明不会大幅度的发展,关于精神的顶点,或者说无限接近顶点的状态,几千年前就出现了。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当我们理解了世界,与世界取得互相谅解,精神得以圆融,不再痛苦,能够平安喜乐却又不是消极的麻木,那就是精神的顶点;只是每个时代遭遇的事情不一样,在每一个生命只有区区数十年的人身上,为他们编织和塑造三观的方式可能都有不同,最终能达到这个境界的则是寥寥无几,但是每一代,那都是我们追求的顶点。
我认为文学是有顶点的,我称唿它为「理论文学」:探索每一种笔法的运用,探索每一种新颖的写作方式、能给人启发的写法,对于精神塑造的探索,以文学架构一个世界,反应深刻而复杂的道理——这样的东西可以得矛盾文学奖,或者诺贝尔文学奖。在此之下,应用文学在其基础上挖掘自身的深度,以文字塑形,传递给他人——传统文学和网路文学皆在此范畴,只是传统文学的传递太少,网路文学则往往缺乏思辨。
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四亿人的大国家,在此之前,我们经历了大量的问题:曾经我是个倾向于公知思维的人,我向往民主,但在这一两年,我想,在如此快速的发展中,这个国家回到世界第二的舞台上,眼下这段时间,若是从后世看来,该算是类似于某某之治的中兴盛世?于是我心里的某个部分开始为自己的国家觉得自豪,某些状态又回到五毛党的位置上,而我仍然向往民主,只是对于民主的想法更加复杂起来:民无能自主,谈何民主?
但无论如何,精神发展仍旧处于低潮之中。
要正确塑造一个人的三观,是有一套方法的,在古代,儒家持续了许多年,他们有了许多的既定经验——且不说儒家最终的好与坏,要将某个人培养成某个状态,儒家的方法已然延续千年——五四运动之后我们打掉了框架(註二),新的框架却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失去了培养一个人的成熟体系。
就如同我学鲁迅一般,我确实看见了问题,但我将问题指出来,我却成了想法不好的那个——老师固然会说是为了我的考试和将来好,但如此一来,精神上的塑造过程也就出问题了,大问题。
我们时常在社会上遇到种种格格不入的东西,我们付之一笑,视若平常,但这些东西会点点滴滴的渗入你的精神里。有一次我跟一个土豪朋友聊天,他说:「我最多的一个月,收入是四百五十万,但我还是觉得不踏实,想赚更多的钱……但赚多少才踏实呢?」
对一些人来说,一个月赚四百五十万仍旧不踏实,这是无病呻吟、矫情,但我想,那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他未必不知道,但仍然只能继续赚钱。
无论贫穷或富有,我们这一代人里,都必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缺失,我们追求某些东西,但追求的东西最终却无法告慰自己,于是在最后,感受到焦虑和生活的重压。
我想将这个问题归咎于三十年来文学圈或者说精神文明的无力上,在最好的期待里,我生活的环境应该给我一个圆融的精神——但我无法指责他们,我甚至无法指责文学圈,因为我们之前的损毁是如此之大。但,当传统文学圈不断贫瘠,他们的道理越来越无法打动人,下一代人的精神文明又该怎么办?
既然拥有那么多的好东西,为何不去研究一下娱乐,研究一下传递,在不妥协的情况下,尽量感染更多的人呢?
前段时间,有一位研究网路文学的教授带的学生在起点发文,一段时间以后不过数百点击——俗称仆街,他们大为诧异,在一些新闻稿上表现出「我竟不能写好网路文学这种低层次东西」的态度——当然,或许不是学生本人的想法,媒体挑事也有可能,但他们的基本态度确实是错的——若大学里能够将娱乐和内涵视为同样重要的文学因素,或许不到十年,眼下的网路文学圈将不复存在。
不过,对于上层人来说,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站在娱乐的一边或是站在内涵的一边都很平常,唯有站在中庸的人,最容易受到打击。
然而这是十四亿人的社会,十四亿人的精神贫困,人们嘲笑家庭主妇看肥皂剧,却从不去主动改变她们,认为这个无法做到;拥有高端精神层次的人们高高在上,彷彿等待着有一天这些家庭主妇忽然喜欢上他们的东西——有可能吗?人们走出学校以后,不存在学习的强制性了,精神贫困也能活一辈子的,只是某一天——或许没有——忽然觉得有些事情缺失了、世界变坏了而已。更何况,在塑造精神的强制性上,就连学校的作用都几乎等于零了。
教科书上的道德文章,对如今的学生到底还剩多少让他们心悦诚服的感染力?
我有一天帮朋友看一篇论文,其中一段如下:
「高等教育处于教育的最高层,起着指导作用,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及水平,往往成为衡量该国教育发展规模和水平的标志,也是该国科学技术、文明程度和综合国力的象征。一个国家的物质文明关键取决于该国科学技术水平,同样,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关键在于该国教育发展的规模、水平,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因此,提高国家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我不是要说这篇论文有多大问题,我颇为在意的是,就算只是作者的疏忽——但是,精神文明在哪里?我们谈论高等教育的时候,为什么只侧重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却是只字未提呢?
用这样的论文来以偏概全,是我过分了,但有一点其实很明显,高等教育对精神文明的塑造,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高。
我们的教育,正处在有史以来最大的问题当中,知识的普及并未真正的提高人们的教育水平,因为教育二字,是要塑造人生观的,要教孩子怎么做人的,而今天,知识的氾滥导致权威的消失,一个十岁的孩子说一句中二的话放在网路上,会吸引一万个同样中二的人过来抱团取暖,于是权威、正确也就消失了。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任何观念都不会得到修正,你想的你说的都是对的,总会有一万个人陪着你——这样的人,长大会怎样呢?
我的后半段成长过程也是这样的。
学校只能传授知识,失去了塑造人生观的力量,社会就更没有了,原本用来塑造精神的思辨和经验只是静静的悬在最高处——为何不将它们加上娱乐的功能,将它们放进普罗大众之中呢?
于是后来,我不再想当传统作家了,对于研究理论的我仍旧敬仰万分,但在其他方向上,我想,我这辈子也可以定下来了,就这么当个媚俗的网路作家,做着吃力不讨好的结合探索工作吧——如果三十年后,有人说他的精神被这个世界塑造成这个样子,文学圈是有责任的,我也只能说,作为十四亿分之一,作为崇敬鲁迅的一个写手,我尽力了。
说完这么冗长的一堆废话,有许多人要烦了,或者已经烦了;但无论如何,三十而立,这些或中二或傻屄或异想天开的东西,是我因何而成为我的思维根系,是我想要留在三十岁这个节点上的东西。
回到最初。
我三十岁,生活有好有坏,仍旧住在那个小镇上写书,时常绞尽脑汁,时常卡文,但因为有书友的宽容和支持,生活终究过得去。身体不算好,偶尔失眠,辗转反侧;若在卡文期,生活便会常常因为焦虑而失去规律。镇子上房价不高,我攒了笔钱,一个月前在湖边买下一套房子,二十五楼,风景很好,一年以后能住进去,我的弟弟就不用睡在阳台上了。
我偶尔出去散步,若是写作顺畅的时候,还能跑跑步锻鍊身体。有时候有一两个朋友,有时候没有,我最常做的消遣是一个人去小镇里的电影院看新上映的电影,观众通常不多,我常常可以包场——幸好我对恐怖片并无兴趣。我的生活圈不大,去哪里都只要步行十五分钟,所以我还不会开车,也不打算学车买车了。
我对朋友时常不能真诚以待,因为脑子里念头太多,用脑过度,接触少的人便会常常忘记,今天有人打电话祝我生日快乐,是个聊过好几次的人,我竟没有存下他的电话号码,名字也忘了。这样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往往尴尬,每感于此,我想最真诚的办法,只能是少交朋友,于是也只好将生活圈子缩小,若你是我的朋友,且请包涵。
当然,关系牢固一点的朋友也是有的,有时候会一块出去旅游散心,但从不赶景点,不愿匆忙。
这似乎就是我生活的全部了。
相对于我玩着泥巴,唿吸着水泥厂的烟尘长大的那个年代,许多东西都在变好。我时常想起在损毁的偏激的人生中养成的一个个的坏习惯,但过去无从更改了。
所以,与其长吁短叹、顾影自怜,不如去做点什么吧。
註一《匆匆那年》,改编自同名小说的中国校园爱情电影,地位与《那一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之于台湾相差彷彿——应该吧。两部我都没看过。
註二广义的五四运动是指自一九一五年中日签订《二十一条》》至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期间,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反思华夏传统文化,追随「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探索强国之路的新文化运动。
图书试读
在这个冬日里,百万人聚集的城池不复往日的喧嚣,北面的城墙下,护城河里静静的结出厚冰,鲜血、尸体、城墙上扔下来的守城玩意儿一半沉入河底,一半突出冰面,在一次次凉了又化、化了又凉的过程里,逐渐形成狰狞无比的雕塑。
厚实高耸的城墙里,灰白相间的颜色渲染了一切,偶有火焰的红,却不显得鲜艳。城市沉浸在死亡的悲切中还不能复甦,绝大多数的尸体在城市一端已被烧毁,牺牲者的家人们领一捧骨灰回去,放进棺木,摆出灵位——由于城门紧闭,更多的小门小户连棺材都无法准备,唢吶声此起彼落,家家户户多是哭声,悲到了深处,则连哭声都发不出来了。一些老人妇女,在家中孩子丈夫的死讯传来后,或冻或饿,或悲凄太过,也跟着静悄悄的死去了。
这样的悲痛和凄凉,是整个城市中从没有过的景象,尽管攻防大战业已停下,笼罩在城池内外的紧张感却是犹未退去,自西军种师中与宗望对阵全军覆没之后,城外和谈一日日的仍在进行,和谈未止,谁也不知道女真人还会不会继续攻打城池。
当初大伙儿与城偕亡的心气劲已经过去了,稍稍缓解之后,痛楚涌了上来,没有多少人再有那种锐气了,城中的人们忐忑的注意着城北的消息,有时候就连脚步声都会忍不住放缓一些,生怕惊动了什么一般。
腊梅花开,在院子的角落里衬出一抹娇艳,仆人尽可能小心的走过门廊,因为正厅里老爷们正在说话。为首的是唐恪唐钦叟,旁边做客的是燕正燕道章。
兽纹铜炉中炭火燃烧,两人低声说话,倒并无太多波澜。
「汴梁一战至此,死伤之人不计其数,这些死了的,不能死得毫无价值……唐某先前虽一力主和,与李相、秦相的许多想法却是一致的,金人性烈如虎狼,既已开战,又能逼和,和谈便不该再退,否则金人必卷土重来……我与希道贤弟这几日时常议论……」
「唐大人、耿大人此念,燕某自然明白,和谈不可草率,只是……李悦李大人性子过于谨慎,怕的是他只想办差,应对失据……此事又不可太慢,若是拖延下去,女真人没了粮草,只好狂飙数百里外劫掠,到时候和谈必定失败……不易拿捏呀……」
「依唐某所想……城外有武瑞军在,女真人未必敢妄动;如今我等又在收拢西军溃部,相信完颜宗望也不欲在此久留。和谈之事,他者尚在其次,其核心一为精兵,二为太原——我有精兵,方能应付女真人下次南来;有太原,此次大战才不致有切骨之失。至于钱物岁币,反倒不妨沿用武辽前例……」
用户评价
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其中对人性的洞察。它没有简单地将人物划分为好人或坏人,而是深入挖掘了角色内心的复杂性。我看到了在利益纠葛面前,人性的善与恶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又是如何在现实的压力下做出无奈的选择。有的人物,在初期可能并不讨喜,甚至让人反感,但随着故事的深入,你会逐渐理解他们的动机,甚至会因为他们的某种坚持而产生共鸣。这种刻画方式,非常真实,也更具感染力。我常常会在阅读中思考,如果是我,在这种情况下又会如何选择?这种引发读者思考的设计,无疑提升了作品的深度。而且,作者在处理情感线时,也显得尤为细腻。那些若有若无的情愫,那些欲说还休的遗憾,都处理得恰到好处,没有落入俗套,反而增添了一种朦胧的美感。总的来说,这本书在情感和人性这两个层面,都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足够吸引眼球,金属质感的纹理,龙纹暗纹若隐若现,再配上那醒目的“赘婿 贰之玖 瑞血丰年”几个大字,瞬间就勾勒出一种大气磅礴、暗流涌动的江湖气息。我毫不犹豫地将其收入囊中,并且在拆开快递的那一刻,就迫不及待地翻开了第一页。那种纸张的触感,油墨的清香,都让我感到一阵久违的阅读的仪式感。我喜欢这种能带来沉浸式体验的实体书,尤其是在这个电子阅读泛滥的时代。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个承载着故事的艺术品,摆在书架上,本身就是一种装饰。我对手工艺人的匠心精神总是充满了敬意,而这本书的装帧设计,无疑体现了这一点。书名中的“贰之玖”三个字,更是带有一种神秘的暗示,仿佛隐藏着某种深层的含义,让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而“瑞血丰年”这个词组,又似乎预示着一场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其中夹杂着家族的荣耀、个人的奋斗,甚至是历史的变迁。总而言之,仅从外观和名字,这本书就已经成功地激发了我所有的好奇心,让我对即将展开的故事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评分我通常是个对情节节奏要求很高的人,如果开头拖沓,很容易让我失去耐心。然而,这本书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出色。它没有过多的铺垫,而是直接将读者抛入了一个充满冲突和悬念的开端。我能感受到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倾注的心血,每一个角色的出现都不是偶然,他们的言行举止都似乎带着某种深意,与整体的叙事脉络紧密相连。我尤其欣赏的是故事中那种不动声色的张力,表面平静之下,实则暗流涌动,危机四伏。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让我手不释卷,总想知道下一个转折点会是什么。而且,作者在描写场景时,也颇具匠心,文字如画,将我带入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仿佛我置身其中,亲历着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我喜欢这种能唤起我强烈代入感的作品,它让阅读不再是被动的接受信息,而是一种主动的体验和探索。这种精妙的叙事手法,让我对作者的功力有了更深的认识。
评分阅读的过程中,我常常被作者对细节的把控所折服。无论是人物的服饰、器物的摆放,还是当时社会的风俗人情,都被描绘得细致入微,仿佛一个生动的缩影,让我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不仅让故事更加可信,也为整个世界观的构建增添了厚度。我喜欢这种能够让我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那个时代的阅读体验。而且,书中对于一些历史事件的巧妙融入,也处理得非常自然,没有生硬的解释,而是通过人物的视角,通过故事的进展,潜移默化地将信息传达给读者,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增长了见识。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是我非常欣赏的。总而言之,这本书在细节和历史氛围的营造上,都做得非常到位,让整个阅读过程都充满了惊喜。
评分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关于“成长”的主题。我见证了主角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逐渐蜕变成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男子汉的过程。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充满了挫折、失败,甚至是对自我的怀疑。但是,正是这些磨难,塑造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教会了他如何面对困境,如何承担责任。我能感受到他在每一次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力量,以及在困境中不断学习和进步的勇气。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在当今社会尤为可贵,也深深地激励了我。而且,书中关于“传承”的描绘,也让我颇有感触。家族的责任,前辈的嘱托,都在主角的身上得以延续。这种代代相传的使命感,让故事拥有了更深厚的底蕴。总的来说,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更是一部关于人生、关于成长的哲学寓言,给了我很多启示。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