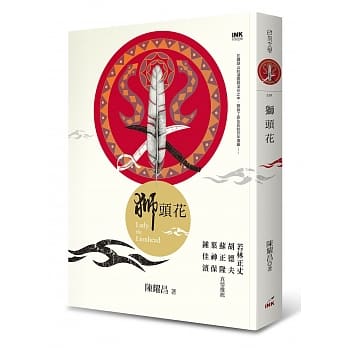

具体描述
转型正义最初始!
原汉从冲突到和解,交织出台湾移民时代里岛屿族群的爱恨情仇
详实描写部落、种族以及互动,
唤回被淡忘的大龟文故事。
「两个世代、四种兵」是十分真实的。如拍打海岸的波涛般,袭击台湾原住民族社会的文明,也包含这样的「真实」。──若林正丈(日本研究台湾政治第一人)
虽然这是一本小说,但是其中牵涉到排湾族的许多典故都是非常真实的,对于半个排湾族人的我来说这不只是必读的书,更是我要学习的精神。──胡德夫(原住民运动先驱)
陈耀昌的台湾历史小说三部曲也让我联想到罗伯特‧哈理斯(Robert Harris)的《西塞罗小说三部曲》(Cicero trilogy)……透过小说的形式,让我们有闻所未闻的新鲜感和震撼。其小说中的故事确实适合搬上舞台,画为漫画,拍成电影。──苏正隆(台湾翻译协会前理事长)
我觉得他的小说,其实是我们的中学生与大学生真正去了解台湾史的最佳入门途径。就像他说的:「要解决原汉议题,请先了解原汉之间的历史。」──钟佳滨(立法委员、前屏东副县长)
《狮头花》不仅有着流畅的故事架构及细致情感的描述,来支撑起故事的架构,背后列强的施虐与殖民社会的苦难,不禁让我们思索这段悲惨的历史,对原住民走出悲伤的历史阴影有何关怀?对我们当今的台湾人有何启示?对我们建构台湾的未来有何指引?──叶神保(排湾族大龟文后裔)
他们试图提醒台湾人,他们的存在与功勋。
在上瑯峤狮头山的蒙雾与溪谷中,原汉从冲突到和解,交织出台湾移民时代里岛屿族群的爱恨情仇,由对抗到和谐的过程。
两千名埋骨台湾的淮军,与雄霸南台湾的「大龟文酋邦」之间,一场可歌可泣的原汉战争,以及一场影响深远的原汉恋情。
2016年台湾文学奖金典奖《傀儡花》作者陈耀昌医师力作,「台湾花系列」第二部。以带浓浓台湾情之笔,重建1875年「开山抚番」时代已被淡忘的「狮头社战役」。更荣获2017年「新台湾和平基金会」历史小说奖。
著者信息
陈耀昌 教授
在医学专业生涯中,完成台湾首例骨髓移植等,荣获卫福部「卫生福利专业奖章」肯定的干细胞名医、教授,退休后另辟高峰,以「台湾最老新锐作家」之姿,每出书必获奖,必为畅销书。
《福尔摩沙三族记》(远流)入围2012文化部「台湾文学奖」
《岛屿DNA》(印刻)2016巫永福文化评论奖
《傀儡花》(印刻)2016文化部「台湾文学奖小说类金典奖」、金石堂2016年度十大影响力好书、2017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入围,并将由公视改编为大河剧。
本书《狮头花》(印刻)未出书已获2017「新台湾和平基金会台湾历史小说奖」
作者写历史小说,均身历其境踏察,而笔下时带台湾情。
请让作者带领您,去挖掘与探访被空白,被遗忘的精采台湾历史,会让您充满惊喜及感动。
图书目录
两个世代、四种兵/若林正丈文 颜杏如译
这一片原住民土地上曾有的故事/胡德夫
狮头花与西塞罗三部曲/苏正隆
两张屏东地图/钟佳滨
《狮头花》序/叶神保
作者的话
前言 淮军与大龟文的召唤与寻觅
楔子
第一部 日本兵:刀挥牡丹望风港
第二部 大龟文:与世无争却见扰
第三部 清国兵:雄师渡海拒倭军
第四部 莿桐脚:是非争议总难评
第五部 沈幼青:开山抚番惜变调
第六部 王玉山:虽约护民却伤仁
第七部 阿拉摆:英雄别爱殉乡邦
第八部 上瑯峤:原汉今日终和议
第九部 狮头花:三千里外却逢君
第十部 胡铁花:泪洒凤山昭忠祠
神鬼任务之一
「凤山武洛塘山淮军昭忠祠」之探访及再现
神鬼任务之二
枋寮「白军营」之外尚有淮军遗冢?
附录 台湾淮军史
图书序言
淮军与大龟文的召唤与寻觅
—我写《狮头花》的心路历程
先说一段灵异故事。后来在我写作过程,灵异的含量愈来愈足,让我深信不疑。
2015年3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日,汉人的元宵节,但对我的意义不同。这是屏东马卡道平埔的「姥祖生日」。在屏东的射寮和后湾,当天有难得一见的夜祭与跳戏。我已期盼经年。补上这一段踏查经历,我的《傀儡花》就可以大功告成。然后3月6日,我打算到屏东牡丹乡的女乃旧社踏查。女乃社就是1874年6月2日牡丹社事件时,日军分三路大举进攻牡丹社群,北路自枫港出发,越过女乃山,所攻破的部落。
那时我心中所构想的「台湾花系列三部曲」,第一部是《傀儡花》,写原住民与洋人的冲突;第二部《牡丹花》,写原住民与日本人之间的冲突。我心中的构想,是以牡丹社事件中,在女乃社被日本兵俘获后,送到日本国内教育改造的牡丹少女「阿台」为主角。至于第三部《胡铁花》,则是借胡适的父亲胡传来贯穿描写清代「开山抚番」政策下的原汉冲突。
当天我搭高铁南下,一大早到了左营。跳戏和夜祭都是入夜才开始。有此空档,我就请朋友帮忙在上午九点半到下午三点半之间,到屏鹅公路沿线踏访「淮军遗址」。
下了高铁,我与高雄好友邱君(《傀儡花》楔子中带我去「荷兰公主庙」的朋友)及潘君(斯卡罗总股头潘文杰第五代孙)会合后,直驱屏鹅公路。
不料车子才上88号公路,就愈开愈慢,然后右边车盖竟然冒出白烟。我们只好下车,在高速公路旁等待拖车。邱君很纳闷,因为这部车在一週前方进场保养。我们到了潘君曾任职的某修车厂,等了一个多小时,确定车子不可能当天修好。于是修车厂慷慨借了我们一辆车,继续行程。
我查到屏鹅公路旁至少有三个清朝官兵墓冢,由北向南分别是1.佳冬昭忠祠,2.枋寮昭忠祠,3.嘉和与莿桐脚之间公路旁的王太师镇安宫。(那时我以为来此的清军都是淮军,后来才知道不然。佳冬的是广东军,枋寮是淮军,镇安宫则为湘军为主。)
容我在此补充说明何以会对「淮军在台湾」这个议题产生兴趣。过去,我们很少听说淮军曾经在台湾轰轰烈烈过。
说起来,这也是才半个月前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机缘。
我家每年春节会出游。但2015年在举棋不定之间,所有旅行社均已爆满。唯一有空位的是「黄山」。
我喜欢古蹟或博物馆,风景对我没有吸引力。黄山行可说是为旅游而旅游。没想到,此行竟改变了我既定已久的写作计画。
黄山之行果然索然无味。还好山下徽州特有的清丽景观让我精神一振。
2月22日最后一天,行程是自合肥搭机回台北。在合肥,有一上午空档。旅行社安排的景点,只有最后的参观李鸿章故宅还算合我口味。李府中展出史料照片图片甚多,我看得津津有味。
近尾声时,有一张「淮军昭忠祠全国分布图」深深吸引了我。我发现台湾竟然也有一个,在凤山。凤山是我外祖父母家,我小学至高中每暑假必到,但我却从未听过凤山有「淮军昭忠祠」。
回到台湾后,我上网查询凤山古地图,果然有「武洛塘山昭忠祠」。光绪三年(1877)建成,依文献记载,祭祀淮军一九一八人。这数字又让我吓了一跳。对照凤山古今地图,发现昭忠祠原址已是民宅,早已不存在了。还有,我从未听过凤山有「武洛塘山」。
我们在教科书上唸到的淮军何其神勇,因此一九一八名淮军战死台湾的数目让我震撼。这至少是牡丹社事件时,日军死亡人数的二倍。史料又说原住民有五个部落被燬,那么原住民被杀的人数应该也很可观。这么重大的史实,我却懵然不知,而即使政党轮替后的中学历史课本也好像未提。
「凤山昭忠祠」已成历史,但我查到当年战场旁边的屏鹅公路至少仍有三个清朝殉职官兵遗址,我一定要找到。而第一个目标在佳冬,我想当然认为也叫「昭忠祠」。
因车子出了状况,原计画十点半到佳冬,变成十二点半,已是公家机关午休时间。街坊及市场父老皆曰佳冬没有什么「淮军昭忠祠」,只有1895年抗日志士的小庙。我们坚持应该有,有年长村民讥嘲:「我自小在佳冬长大,说没有就没有。」 后来到了一个路口,见一老者坐在路旁吃便当,我们上前请教,竟是玉光村村长。他不确定地说:「你们说的可能是一个很偏僻的小庙,骑摩托车十分钟左右。我也不敢确定地点,但那好像是纪念抗日志士。」
又是抗日志士。我们都好失望,但还是打算去看看。他指了一个方向。称谢道别时,我突然心血来潮,取出名片,说我是台北来的,本行是台大医师,探访是为了写小说。
他瞄了一眼名片,突然问:「你熟悉某某医师吗?」我说:「是我大学同班同学,还是同寝室好友。而且很巧,今天因为我要造访他家乡,我俩还在LINE上聊了一阵。」村长一笑:「我是他小学同学。」
距离骤然拉近,老村长表示乐于以摩托车带路,我们大喜。果真还不好找,绕来绕去来到荒郊野外一个只有约三公尺宽的小庙,上题「忠英祠」,而不是「昭忠祠」。神桌上二个牌位,后面的老旧石牌位刻着「皇清 振字 福靖 营 开山阵亡病故员弁勇丁神位」,我高兴地无以名状。福靖营正是王开俊麾下营号。但另有一座相当新的「抗日志士」祖先牌位,几乎完全遮住了旧牌位。难怪佳冬村民皆不知小庙原旨,而有所误解。(附图)
因为此次行程主要是与原住民上山到女乃社,于是我在台北出发时,随手带了数包我自黄山行买回的花生。细心的邱君则主动为我准备了两瓶洋酒。我拿出花生与酒来祭拜。合掌而拜时,我又心里一震。天啊!怎会这么巧,我竟会刚好带了安徽出产的花生,还有洋酒,来祭拜一百四十多年前在台殉职的安徽淮军(註1:后来,我查知此处福靖营为台湾镇总兵张其光属下李光之部,属广东兵,在光绪三年左右因开路殉难,与王开俊无关。)!
第二个目标是「枋寮昭忠祠」。在枋寮我们第一位问路的年轻女性竟然二话不说,马上开着车带领我们去。于是我们到枋寮后十分钟,就到了北势寮的白军营。原来当地人叫「白军营」而不称「淮军昭忠祠」。但祠堂内有「淮军义祠」及「枋寮昭忠祠」的匾额。不用说,如果没有人带路,一定要摸索很久。这个白军营规模更大,由其庙后墓龟之隆起,可以想见埋葬人数至少上百名。于是我也以安徽花生及洋酒祭拜了他们。这次是正牌「安徽淮军」。
后来我查到,这个白军营一共埋葬了七百六十九名淮军,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抵台迄光绪元年(1875)元月,狮头社战役前在凤山病死的淮军(註2:后来我在2016年10月11日再度造访白军营,竟巧遇白军营改建者柯三坤老先生,他迫不及待告诉我他的建庙过程,也充满灵异。他挖出的骨骸四百余,分四列整齐排列,他以庙侧碑文记载此事,见第二十一页照片)。
第三个「王太师镇安宫」依我查到的网路资料似在山边,但我们当天未能找到,后来多次寻找也都落空。直到2016年1月31日经枫港耆老之助才找到。竟然是在屏鹅公路旁的小巷内海边,是2001年迁建的。建筑外观是民房,如果不是有香炉与塔,看不出是庙宇,有些怪异。
第二、三天我终于如愿到了女乃社。与我们同行的牡丹村村长说,这个女乃旧部落已废弃多年,连他们都是第一次来此。换句话说,自1874年到2015年,已经有好久好久没有人迹。我们沿着四重溪溯溪而行,披荆斩棘,终于到了在1874年6月2日被北路日本军焚燬的牡丹人旧居。村长在进入旧部落之前,虔诚祷告,表示希望没有打扰到祖灵。然而,当晚与翌晨,我在女乃社诸事不顺,相当突兀。
3月5日至7日的不寻常过程,后来逐渐在我心中发酵。首先,我想我是得罪了女乃社的祖灵,或者是女乃社祖灵不喜欢我把他们写入小说。我领悟到,不管是整个女乃社的亡灵也好,「阿台」个人也好,对祂们而言,1874年是悲痛、残酷与不堪回首的过去。祂们宁可隐匿于深山之中,伴着当年的石屋残柱而不受外界打扰(更不愿被公开、回顾)。
相反的,另外有一股冥冥之力,牵引我到安徽,到合肥,然后到佳冬,到北势寮。如果我们车子没有莫名其妙故障,我们很难如愿找到忠英祠及北势寮白军营。而且我们神差鬼使带了安徽花生,带了酒来祭拜。这些淮军亡魂给台湾遗忘了超过百年之久,他们在天上或地下岂能甘心。他们埋骨台湾,然而纪念他们的凤山淮军昭忠祠,只存在了三十年左右,就为日本人夷平,遗骸不知何在。如今台湾二千三百万人包括台湾史学者在内,几乎无人重视凤山曾有淮军昭忠祠的存在。至于白军营及忠英祠,香火少得可怜,甚至给当地民众的抗日志士祖先牌位掩盖了。
试站在这些淮军的立场,他们当年来台,是为台湾居民对抗日本人。后来投入狮头社战役,也是为了台湾居民。他们为台湾人而埋骨异乡,后世台湾人却毫不知晓,也不领情,他们岂能瞑目。更不堪的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因为时代的变迁,这个岛上正逢原汉关系的反省与再出发,在转型正义的思潮下,大家因为同情原住民被百年欺凌,因此开始谴责郑成功为入侵者,也责怪「开山抚番」始作俑者沈葆桢,对前朝的清廷更是毫无好感。可是淮军将士何辜?他们也不愿渡海,更不愿打仗。他们也是受害者。(註3:有关凤山「武洛塘山淮军昭忠祠」的始末,后来就继续寻访,略有所成,过程也充满神奇,请见第三八七页附文。)
因此,他们试图提醒台湾人,有关他们的存在与功勋。
于是,我惊悚了。我也必须承认,直到去寻访忠英祠与白军营的那一刻,我心中还是有偏见,认为这些死在狮头社之役的清军,和死于牡丹社事件的日军一样,都是一丘之貉的外来侵略者,而非正义之师。这次踏查,促使我重新省思。来台的淮军,在同治十三年面对犯境台湾的日本,是奉命保国;在光绪元年,出兵狮头社,是奉命卫民。他们尽忠职守,竟因而埋骨异乡,且又为了后世的意识型态而蒙上侵略者污名,怎能不抗议,怎能不发声。我一向倡导日本大河剧的「只要忠于职守就是好人」的价值观。怎么可以在这方面,竟那么「媚俗」(Kitsch,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的用词)。
回顾历史,我们也许可以质疑狮头社之战是否是可以避免。我们自史书来看,可说是王开俊擦枪走火酿的祸。而沈葆桢是否反应过当,使抚番变剿番,也可以讨论。但史论不可让这一九一八位淮军蒙受不名誉或永远淡忘。
尤为讽刺的是,后来牺牲的一九一八名淮军,埋没于荒烟蔓草,不存于后人记忆,也消失于史册典籍。而一开始就被当时《申报》批评为滥杀惹祸而自身也惨死的游击小官(相当于今之「营长」阶)王开俊,反而一人成神,独享人间烟火。后来2016年1月31日,我终于在屏鹅公路嘉和海边近七里溪河口找到了这一间迁建后的王太帅镇安宫。那是光绪元年四月二十日左右,淮军将找到的九十七人尸骨与王开俊头颅后合埋之处,故建有塔,并有「王」字标示。更妙的是,我之前在屏鹅公路的五路财神庙旁,也找到了小神座「五营元帅」、「保家卫民」,我相信也是王开俊。因为王开俊带领一营「五哨」,于是被民众夸大成「五营」,而也由「游击」晋升为「太师」(《封神榜》的大官)。
如果张光亮、王德成、田勤生等殉职将士地下有知,当然是不服气的。他们之死可说是为王开俊所累。而如今王开俊独享建庙祭祀而他们却遭埋没、遗忘,情何以堪。
于是我渐渐改变想法,决定不写牡丹社事件而改写狮头社战役,就是这本《狮头花》。因为在狮头山的蒙雾与溪谷之中,有太多遭埋没的英魂,有太多给遗忘的台湾历史,有太多的血泪与反讽。
*
然而,更艰鉅的寻寻觅觅是对交战另一方的大龟文踏查。因为我对大龟文知道甚少。首先是,一百四十年后,「大龟文」的名词不见了。原来的大龟文,现在分属屏东狮子乡与台东达仁乡。但是摊开地图一看,除了南回铁路小站的「内狮」车站外以及一个「内文」,找不到当年狮头社战争的痕迹。内狮,顾名思义,不是应该在内陆山中吗?怎么跑到海边来了?而外狮呢,怎么不见了?内文在当年是大龟文两大统治家族逻发尼耀及酋龙的大本营,结果大龟文名号被日本人废了,改称「内文社」。这里在日本时代大正年间,也发生抗日的「南蕃事件」。如今地图上内文犹在,但显然已是旧部落废墟。逻发尼耀后人已迁到台东安朔及屏东东源。至于酋龙家族的子弟,则已搬迁到中心崙。网路上仍以「大龟文」为名的文章,大体就是出自逻发尼耀子弟张金生与叶神保两位政大民族所的博士。
其次是,当年的战场在哪里?如何去找出「领导抗战」的大龟文大头目名字?我写《傀儡花》,在罗妹号事件与南岛之盟中,斯卡罗卓杞笃总股头之名早已如雷贯耳;十九世纪的来台西洋人士对卓杞笃多有描述。只差他早死了几年,未能像他的养子继承人潘文杰,留下许多照片与故事;也不像遭日本人杀害的牡丹社头目阿禄古,因而名留青史。但上瑯峤大龟文要到1898年鸟居龙藏带着他的助手森丑之助才蜻蜓点水探访过,外界对大龟文的文献记载极少。
我朝思暮想的是,以部落酋邦对抗大清帝国的大龟文总头目大英雄,名号为何?我首先想到的方法,是去请教现在的「大龟文国王」张金生。于是2015年7月18日,那个夜凉如水的晚上,张金生与我在他的安朔村「萁模文化园区」煮酒论英雄祖先。「国王」告诉我,大头目的弟弟死在那个战役中。有了这样的讯息,我回到台北之后,就把当年大龟文狮头社战役前后的沈葆桢及其他台湾官员奏文找齐。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在浩瀚文字中,给我找到那个关键人名。在光绪元年四月十五日夜至四月十六日晨最激烈的狮头社决战,相当于1875年5月21日上午,在内狮部落英勇成仁的大龟文头目之弟,叫「阿拉摆」。
光绪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沈葆桢《淮军攻破内外狮头社折》:「自卯至巳,贼始破,计斩悍番六、七十名,内一名名阿拉摆,龟纹社番酋之弟也」。
其二是在上述战役大约一个月后,清廷终于和大龟文人议和,当时在台淮军提督唐定奎在「胜利」之后向大龟文提出七条约定的过程,曾提到许多番社头目的名字,中间最重要的是「野艾」,后来立为「大龟文总目」。
那是沈葆桢在另一篇奏文,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三日,《番社就抚布置情形》:「十二日,枋山民人有程古六者,带至内龟纹社番目野艾、外龟纹社番目布阿里烟;又有射不力社番目郎阿朗者,带至中文社番目龟■(口六)仔、周武滥社番目文阿蛋及散番等百余人款营乞降。……以龟纹社首野艾,向为诸社头人,拔充总社目统之,着照约遵行。所统番社如有杀人,即着统目交凶;如三年之内各社并无擅杀一人,即将总目从优给赏。其狮头社余孽,探悉窜伏何社;即由何社限交,不许藏匿。野艾及各番等均愿遵约。」于是我可以确定在狮头社战役被封为「大龟文总目」的叫作「野艾」。(在小说中,我把「野艾」改为「遮碍」,请见首页:〈作者的话〉中的说明。)
「野艾」及「阿拉摆」就是我要进入大龟文历史的两个关键人名密码。除了文字搜索,现场踏查更是我的最爱。我的随身袋内永远带着那张被我翻得快要解体的大型南部屏东地图。我走入屏鹅公路两旁的每一个溪谷:枋山溪(大龟文溪)及其支流阿士文溪、卡悠峰瀑布(内狮瀑布)、七里溪、枫港溪,终于对当时的部落、战场与行军路线大有概念。后来,我又得以参加逻发尼耀家族及萁模族文化发展协会主办的「排湾族历史文化学术论坛」,收获甚大。再加上我收集的种种清代文书《甲戌公牍钞存》、《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沈文肃公牍》……,以及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翻译日本人所着的《处蕃提要》、《风港营所杂记》及近代《枋山乡志》等,我觉得我已经可以下笔来重现台湾史这段可歌可泣的故事了。
早已有心理准备,写原汉冲突的小说极难拿捏,将是吃力不讨好。我的小小心愿是,希望经由这部小说,能还原1875年的大龟文和淮军战争的原貌。而淮军并非战争发动者,他们是奉命上战场,战后即班师回乡;战争的发动者,算是沈葆桢,但那也较接近是擦枪走火,而非蓄意。在我眼中,双方各有立场,都是英勇、尽责的。只能说,那是移民社会历程中的不幸与无奈。这是一场双方都死伤惨重的战争。我认为我们应该为大龟文的殉难者立碑,为阿拉摆立碑,在当年的古战场立碑,供台湾人子孙凭弔、反省。淮军虽然还有「白军营遗址」,我也认为他们应更受到尊重。到屏鹅公路两侧,对「狮头社战争」的双方现场凭弔,应该是台湾人中、小学历史教育中很重要的一课。甚至,我希望政府明令,将因对抗汉人、保卫家乡而英勇成仁的阿拉摆及其他七十多位原住民英雄的死难之日,5月21日订为「原住民英雄日」或「原住民殉难日」,全国放假一天,以兹纪念。
我喜欢举日本人现在看明治维新的观点来看历史人物。日本人对拥幕派的土方岁三、松平容保、近藤勇等,也充满敬意;对当年「造反」的西乡隆盛,其评价也高于当代政治正确的大久保利通。「人格」、「尽忠职守」才是评价关键,不是「立场」或「成就」。当然因为1875年的战争,从此开始了原住民的百年伤痛,「你们的荜路蓝缕,我们的颠沛流离」。这确实是移民者后代今日需反省,要道歉,需还给原住民的公道。但恩恩怨怨的结局,不应是为了要算清总帐计较是非,而是要双方和解,要多元文化,要族群共荣。也许上天要开山抚番一百四十年后的台湾,选出一个原汉混血的台湾总统来执行原汉转型正义,正是要提醒我们,当年淮军与大龟文战争的双方,如今都已经是台湾人的祖先。1874年以后调派来台的一万多名以上或御外或剿番的军队,有不少后来就定居在台湾民间,而成为台湾人多元祖先的一部分。而当今台湾总统就是当年的开山抚番指标战役之后,大龟文与清军原汉和解而通婚的后代。这莫非是冥冥中的天意?
历史往往要在沉淀之后,才让人恍然大悟。
2016年9月底
图书试读
枫港德隆宫外,锣鼓声喧天价响,围观的不但有大批民众,还有电视台的卫星转播车,把小小庙口围得水泄不通。
寺庙内,穿着湖绿色夹克的女性总统候选人,捧着大束鲜花,向神明恭恭敬敬行礼。在幕僚及随扈的簇拥之下,她缓缓自庙里走出,站在庙口台阶上,一脸自信,接受群众欢唿。披着红色布条的寺庙主委站在她身旁,高举双手,兴奋唿喊:「五府千岁降旨,我们这次一定当选!」民众马上也跟着兴奋高唿:「冻蒜!冻蒜!」
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与响彻云霄的欢唿声中,女性总统候选人满脸笑容,接过麦克风,向群众挥手致词。她的语气却是出奇平静:「我们誓言要点亮台湾。总统竞选的最后一里路,现在,自枫港,我最爱的故乡-出-发-!」
离枫港几十公里外的台东安朔,白发苍苍却依然壮硕挺拔的他,满意地看着这个电视的实况转播镜头,眼眶微湿。他自一大早就守着电视,终于让他等到这一刻。去年年底,这位女性总统候选人来到屏东狮子乡,公开向群众及媒体宣布,她有来自狮子乡的四分之一排湾血统,并且亲笔在表格上写下她的族别是「排湾」。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成为她的死忠支持者。他没想到,在他有生之年,有幸目睹这样的镜头。排湾出头了,大龟文出头了。这个明年很可能成为总统的小女生,公开表示以拥有排湾血统为荣,他感动了。尽管只有四分之一,或是有些人说的八分之一,他已无憾。
「大龟文」或「大龟纹」(註1:大龟文:Tjaquvuquvulj。)这个名称,在十七世纪荷兰时代文献即有记载。大龟文的祖先们经过漫长的迁徙与整合,数百年来在率芒溪以南,枫港溪以北之间的枋山溪(大龟文溪)的山林与河谷,再加上东部太平洋岸阿塱卫溪流域,建立了一个超级部落联合体,被称为「大龟文十八社」或「上琅峤十八社」,事实上已具有族邦,甚至小王国的雏型。
回忆历史,让他痛心。因为但大龟文之名在最近一百年已不复见于官方文书,也在民间消失。几十年来,他一直自称为「大龟文王国国王」。其实,他的真意不在国王或王国,而是为了保存「大龟文」这个祖灵留下来的宝贵称号。
用户评价
我必须说,这本书带给了我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它的叙事方式非常独特,像是层层剥茧,不断地将真相展现在读者面前。我不得不承认,在阅读过程中,我曾多次猜错情节的发展方向,这反而更加激发了我继续读下去的欲望。作者的逻辑构思非常严谨,每一个线索的铺陈都恰到好处,最终汇聚成一个令人惊叹的结局。我特别欣赏作者对于人物塑造的功力,那些角色立体而饱满,他们的动机和行为都令人信服,即使是那些看起来有些“极端”的角色,也能从他们的经历中找到一丝共鸣。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情节的跌宕起伏,更是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它探讨了许多复杂的问题,例如信任、背叛、救赎等等,并且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而是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我常常在阅读时停下来,思考书中人物的处境,以及自己会如何选择。这种参与感让我觉得这本书不仅仅是在“读”,更是在“经历”。我强烈推荐给所有喜欢深度思考和挑战思维边界的读者,相信你们一定不会失望。
评分这是一部充满诗意的作品,语言的运用堪称艺术。作者的文字如同涓涓细流,缓缓地流淌过我的心田,留下淡淡的余韵。我非常享受阅读时那种宁静而优美的氛围,仿佛置身于一个由文字构建的梦境之中。故事的情感表达细腻而含蓄,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有着直击心灵的震撼。那些微小的感动,那些不动声色的悲伤,都通过作者精妙的笔触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我常常在读到某个句子时,忍不住停下来,细细品味其中的意境,感受作者想要传达的情感。这本书让我重新认识了文字的力量,也让我对生活有了更深的感悟。它教会我如何去感受那些被忽略的美好,如何去体味那些细微的情感。它不是那种让人兴奋得手舞足蹈的作品,而是能够沉淀下来,让你在心中慢慢回味,并且久久不能忘怀的。对于那些追求精神享受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绝对是不可错过的选择。
评分这是一本真正触动人心的作品。我常常在午夜时分,趁着月光,捧着这本书细细品读。那种感觉,就像是与一位老朋友在静谧的夜晚进行一场深刻的对话。故事中的人物,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挣扎与坚持,都仿佛真实地发生在我的眼前。我能感受到主人公在逆境中那种不屈的韧性,也能体会到那些细微的情感波动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作者的文字非常有画面感,每一次的转折都像是精心设计的伏笔,让我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我尤其喜欢书中对细节的刻画,每一个场景的描绘,每一个对话的设置,都充满了匠心。读完这本书,我久久不能平静,脑海中不断回响着书中的情节和人物的命运。它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思考生命的意义。这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并且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发现的书。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对生活的感悟。我会被书中那些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情感所打动,也会被那些看似平凡却又充满力量的细节所感染。它让我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了一片宁静的港湾,让我得以暂时放下烦恼,沉浸在阅读的美好之中。
评分我迫不及待地想和大家分享我对这本书的喜爱。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的真实性。虽然故事可能发生在虚构的背景下,但是人物的情感和行为却是如此真实,如此贴近我们的生活。我能够在书中的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也能够在他们的经历中找到共鸣。作者的语言风格非常朴实,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却充满了力量。他用最直接的方式,触及了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我被那些平凡人的坚韧所感动,被那些细微的善意所温暖。这本书让我明白,生活中的英雄,往往就隐藏在那些最普通的人群中。它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它不是那种能够让你逃离现实的书,而是能够让你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更加热爱生活。我真心推荐给每一个想要寻找力量和温暖的读者,相信这本书一定会给你带来惊喜。
评分我被这本书所蕴含的宏大世界观深深吸引。作者构建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平行宇宙,其深度和广度都超乎我的想象。每一个设定都经过了精心的打磨,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逻辑性,让我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创造力。故事的推进方式也很有趣,它不仅仅是线性的叙事,而是通过多视角的切换,将整个故事的全貌逐渐展现在读者眼前。这种叙事手法让我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人物的行为和动机,从而对整个故事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尤其喜欢书中对于历史、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深度挖掘,它们不仅仅是背景的衬托,更是故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这本书让我看到了文学的无限可能性,也让我对未来产生了更多的憧憬。它不仅仅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更是一种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一种对人类自身潜力的挖掘。我强烈建议所有对科幻、奇幻题材感兴趣的读者,不要错过这本史诗级的作品。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