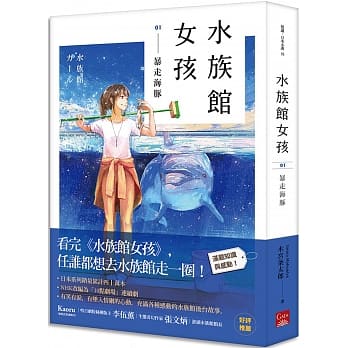具体描述
想到这第五个孩子,她没有爱,也没有感情, 她恨自己竟没有半点正常的情分, 令她夜夜惊醒的,只有罪恶感和恐惧…… 吴尔芙之后,不能不认识的重量级女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代表作 ▍极限揭露人类隐而未显的与恶的距离 ▍女人被爱勒索的酷烈时代 「在我们被撕裂、被伤害甚至被摧毁的时候, 重塑我们的,是我们的故事,是讲故事的人。」──多丽丝‧莱辛 海莉一直相信,这个小怪物是来伤害她的, 现在却怎么也没有这种感觉。 她的心里只有怜悯:可怜的小怪兽啊, 他的母亲竟是这般的讨厌他…… 一个粗暴、野兽般的孩子降临人世,拧转所有家庭成员的心,一片乐土从此倾覆。 班,海莉和大卫的第五个孩子,长相古怪、性格暴戾。他镇日怒吼咆哮,学会的第一句话不是「爸爸」、「妈妈」,而是祈使的命令句:「我要蛋糕。」 面对这个家族里人人回避的孩子,海莉既想守护他,却又暗暗希望他从高处摔落、被车撞死。她那出于本能的母爱存在,但不知从何开始…… 本书探讨阶级社会里,面对异己的矛盾与拉扯,以及母爱的在与不在──「寻常」是什么模样?无知之中,你的宽容还宽容吗? 一部认识莱辛、亲近莱辛的经典之作。 文坛推荐 杨薇云(元智大学应用外语系、淡江大学英文系 兼任副教授) 卢郁佳(作家) __专文作序 李欣伦(作家) 颜择雅(作家、出版人) 郝誉翔(作家、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教授) __莱辛迷一致推荐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
二○○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近几十年来声誉最为卓着的作家之一。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如是形容:「她是描述女性经验的史诗级创作者,她带着怀疑精神,用火一般的热情和想像力呈现一个四分五裂的文明供人们审视思考。」
除了获颁英国最高荣誉勋位奖与最高文学奖项之外,她也获得大卫柯亨英国文学奖、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加泰隆尼亚国际奖,以及杜邦文学终生成就金笔奖。
二○一三年十一月,莱辛逝世,享年九十四岁。
本书续集"Ben, In the World: The Sequel to the Fifth Child"中文版预计于二○二○年出版。
译者简介
余国芳
中兴大学合作学系毕业,曾任出版社主编,目前是自由译者,有《大鱼老爸》、《在地图结束的地方》、《爆醒恶梦的第一声号角》、《屠夫男孩》、《冥王星早餐》、《慾望的盛宴》、《辉丁顿传奇》、《外出偷马》、《能不能请你安静点?》、《大教堂》、《新手》、《需要我的时候给个电话》等超过四十部文学与非文学译作。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
二○○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近几十年来声誉最为卓着的作家之一。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如是形容:「她是描述女性经验的史诗级创作者,她带着怀疑精神,用火一般的热情和想像力呈现一个四分五裂的文明供人们审视思考。」
除了获颁英国最高荣誉勋位奖与最高文学奖项之外,她也获得大卫柯亨英国文学奖、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加泰隆尼亚国际奖,以及杜邦文学终生成就金笔奖。
二○一三年十一月,莱辛逝世,享年九十四岁。
本书续集"Ben, In the World: The Sequel to the Fifth Child"中文版预计于二○二○年出版。
译者简介
余国芳
中兴大学合作学系毕业,曾任出版社主编,目前是自由译者,有《大鱼老爸》、《在地图结束的地方》、《爆醒恶梦的第一声号角》、《屠夫男孩》、《冥王星早餐》、《慾望的盛宴》、《辉丁顿传奇》、《外出偷马》、《能不能请你安静点?》、《大教堂》、《新手》、《需要我的时候给个电话》等超过四十部文学与非文学译作。
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推荐序
你想勒索爱情、勒索母爱,整个社会都会来帮助你
卢郁佳(作家)
芭芭拉.金索沃的小说《毒木圣经》(The Poisonwood Bible)描述比利时白人传教士家庭设法教化刚果殖民地黑人,文化鸿沟的悲剧。当中冷眼观察全局的女儿艾达,真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名英军因伤致残,娶了在医院结识的英国护士,战后在今天伊朗的英国帝国银行工作,生下莱辛。风闻许多人种玉米致富,他们全家搬到非洲的英属殖民地罗德西亚(今天的辛巴威)种玉米,却歉收贫穷,父亲无法适应当地。母亲则想教化黑人,当然也要把莱辛变成淑女,送她进天主教女校,听修女满口地狱恐吓学生。莱辛十三岁眼疾辍学,阅读伦敦寄来的小说自娱:狄更斯,沃尔特.史考特的浪漫冒险故事,史蒂文生《金银岛》,吉卜林,D.H.劳伦斯,斯汤达尔,托尔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她十五岁离家当保姆,读遍雇主政治、社会学书籍,跟雇主的姊夫上床,开始写小说发表在南非杂志上。当过电话接线员、速记员等,她说像地狱般孤独。十九岁嫁人,生下一子一女,私奔离婚。二战时在左翼读书会加入了南罗得西亚共产党,嫁给德国难民,然后离婚带着幼子移英国。穷得行李只有小说《青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的稿子,写一桩黑人男仆杀白人主妇的命案,以殖民地种族真相震动英国,一书成名,后来被南非和罗德西亚列为黑名单禁止入境。她加入英国共产党,后来因为苏联镇压匈牙利而退党。
莱辛此刻能出现在读者面前,绝不是来给体制锦上添花,是杀出血路、闯过地狱来的战神。她是文学上的暴民,与维吉尼亚.吴尔芙和西蒙.波娃并肩站在抗议队伍第一排。生为女人等于在殖民地做个黑人,但是,很少人愿意承认。莱辛《一封未投邮的情书》(An Unposted Love Letter)里的〈十九号房〉描述一对男女结了婚,妻子抛弃事业,实现家庭美梦,在郊区买大屋,生下一群孩子,被育儿和家务摧磨辗压。她设法适应,所有女人不都这么习惯了吗?她去了小旅馆开房,每早十点到下午五点窝在藤椅上放空。但是,她还得向丈夫伸手要钱付给旅馆。丈夫起了疑心,她为保住净土,谎称外遇,压力步步进逼。结局是她在旅馆房间开瓦斯自杀。
莱辛写女性经验,力道像空袭轰炸读者。在砲弹落下的当场,你会先听到一种震耳欲聋的寂静,像是世界空了。过去以后好像环境没有改变,然而身边的砖瓦却无故粉碎,如雨纷落,梁柱崩塌,撕开头顶屏障,裸出蓝天。原本读者置身于看似和谐的社会关系,但从翻开莱辛起,这种和谐维稳再也没有读者的立足之地。
《第五个孩子》在精采情节下就暗藏了颠覆世界的力量。这次出版,正值台湾社会透过《背离亲缘》(Far From the Tree)、《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情绪勒索》等畅销书集体审视原生家庭的伤害,我感激有生之年我终于成长到足以明白莱辛的讯息。读第一遍,这是个天真夫妻遭遇不幸的故事──第五个孩子出生就有暴力倾向,智能不足,像苹果日报「人间异语」。莱辛冷静的口吻令人感到类似公平的事物,轮流呈现每个角色的逻辑、喜恶,不扭曲,没有邪恶,悲剧只是命运无常。
读第二遍,瞬间房里所有盖在家具上的白布都掀开了──结局以后见之明迅速放大角色的颟顸,和他们拒绝面对的真相。极限揭露人隐而未显的本质,在这种X光射线照耀下,角色变形了,变得粗重庞大,他们的身躯像高楼投下阴影,笼罩读者;话声变得遥远尖锐,像是从浴缸水底下听客厅传来吼叫。莱辛的反讽笔触,像是让读者接手、凑上高倍望远镜,看角色说话时鼻头的痘疤怎样随着怒气发红,看见他的鼻毛怎样随着唿吸戳颤,甚至望远镜还变成大肠镜,一路看进肠壁。
小说把一层层的布花瓣叠起来,从中央一针戳透收紧,平面就辐射绽开球形花朵。布片就是「派对」这个群众之眼:最初邂逅的公司派对,呈现男女主角和外界互贴的标签。然后,每年过节一批亲戚来住上两週见证大家庭温暖幸福,亲戚和夫妻俩互贴标签。最后,欢乐派对变成海莉面对体制权威,求助医师、儿子校长召见她兴师问罪。海莉和特殊儿子班的独处互动,实际由背后这一层层互动所形塑。拉紧层瓣的缝线,就是别人怎么看夫妻俩。从外界观感产生的自我形象,成为主角斡旋的战场。海莉不断和这些扯她后腿的痛苦自我形象搏斗,从派对开始一路寻求认可,到认清她所要的只是对方承认问题,和她一起分担,这就是震动天地的女性成长。
●
小说展示的重点并非要不要生,而是众人如何做这个决定。两人想要很多孩子,至少六个。是谁想要?开头蓄意模煳,说两人都想要。接着更暧昧,「要不要继续生孩子」的问题,竟是通过「过节要不要邀请大批亲戚来家里住」的问题提出来探讨,而变成「哪些人必须出钱出力养孩子」,变成「要不要把班送走」。决定要不要生,像决定要不要邀亲戚过节,海莉无法说出要求,而以「不办宴会,孩子会失望」、「医生说班很正常」暧昧表达。海莉无权为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作主。
小说前半写海莉一意孤行多产,享受孕妇像女王受宠。众人怪海莉任性,没人把矛头指向大卫。后来海莉违逆大卫,坚持要生,大卫忍怒不发。海莉生下特殊儿,要求再多生几个。大卫的反应揭露了「生很多孩子」是大卫的期待。两人一见钟情,是海莉从雅房分租逃进大卫的小屋同居,而不是相反,说明了两人的权力关系。大卫不满双亲离婚后忽略他,决心以组织家庭修正自己的童年悲剧,「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女人。」「他的妻子在这方面必须像他:她必须知道快乐在哪里,该怎样维护。」莱辛用「什么」、「哪里」这幅无所不在的白布,遮住了大卫对海莉的爱情进行勒索的事实。大卫描述安全感的方式,是他少时的房间,这房间要他无止境扩充,大房子只是无穷饥渴在现实中有限的投影。
如果我们有权自主做决定,也就有权更改这决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改变心意。海莉虔诚追随大卫主导,最后跟丢了,像受难圣徒般死守任务,甚至为此反抗大卫。婚姻成了一场双人羽织表演,看起来是一个人在吃东西;羽织底下却是两个人,海莉的双手盲目在餵大卫,大卫说够了,但海莉继续。因为开头饿的人是大卫,所以进食无关海莉饿不饿。即使大卫饱了,海莉也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难以接受。因为海莉仍然饥饿,双人羽织从没餵进海莉的嘴。
两人生孩子,不是伴侣之爱扩及爱孩子,而是向父母讨爱。第一,大卫无法接受父亲施惠,只有借口养儿装作勉为其难接受。海莉母亲照顾唐氏症外孙女、外孙,代替亲近女儿,三个女儿也以争夺母亲顾孙来争夺母爱。这种爱就算讨到了,也不会饱,因为当事人不知道自己在讨什么,也不觉得被爱。第二,大卫无法亲近任何人。他跟海莉相处轻松,因为自从第一胎出生后,夫妻就没有单独共处过。生孩子免除了他面对妻子的折磨,掩盖了问题,让海莉饿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在挨饿。情感交流像洗钱般不停转换名目,结果都在孤立海莉。
孩子遇到问题,整个社会都推给母亲海莉,要她负责解决。但海莉得从小有母亲支持,才能抗衡大卫。得有大卫合作,才能抗衡特教体制。抽掉这两个心理资源支柱,海莉就被困境压死。社会诉诸母爱应该解决一切,就是对母爱进行勒索。
●
来自非洲热烈荒野的莱辛,向晚披襟眺望席卷资本主义社会的情感匮乏冰风,写下如此悲切之笔:
海莉想婚后先工作两年存钱再生,但因大卫坚持而怀孕。大卫「放肆、毫无忌惮的大笑,完全不像平常那个谦沖、知趣、得体的大卫」,笑容里的祕密隔绝了海莉,使她不安。这是大卫的真正面貌,只因压抑而沦为施虐。
「孩子们的原始野性,前一刻还在他们的血液里跳动;但现在必须把原始狂野的一面放下,才能够重新回归家庭。」海莉与大卫「两个成年人坐在那里,温顺,居家,甚至可怜,因为野性和自由早就离他们远去」。
海莉求助于女医生吉利,医生归罪她搪塞,然后「突然、出乎意料地,毫不掩饰地透露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她是个端庄的中年妇人,她的人生充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在这一个瞬间,一股不受控、不合法理的忧虑显露了出来」。
职场,家庭,生活,台湾的我们正在经历情感的冰河期,女人被爱勒索的酷烈时代。《第五个孩子》说出了人们只能模煳感觉的事,只能在梦中一瞥随即遗忘的真相。
因为我们需要莱辛,所以莱辛在这里。
恶何以形塑?
杨薇云(元智大学应用外语系、淡江大学英文系兼任副教授)
恶为何会出现?什么时候出现?经由什么样的原因,形塑成形,造成伤害死亡,社会秩序的崩解?这问题,从古至今困扰了不知多少领导者、宗教家、道德家、哲学家、心理学家、法律人。最近刚刚落幕的公视年度大戏《我们与恶的距离》,促使台湾无数的观众共同省思: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与恶的距离有多近?
恶这个最难捕捉的人性元素,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的《第五个孩子》故事中,有着非常细腻的描述与诠释,看过《与恶》的观众们,绝不可错过这部精准刻划出边缘人的极品。阅读此书,读者可以欣赏莱辛精简犀利透澈的文字,体会到边缘人在正常人的敌视中,孤独生活的痛苦,也可看到社会文明的主流力量,为了维护正常的生活,不惜除去一个异常小孩的残酷。人与恶的距离,很难评断,但是在文明道德价值混乱的时代,维护人道的底线,为主角奋斗的目标,也是读者关切的重点。
●
二○○七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颁赠诺贝尔文学奖给八十八岁的莱辛,委员们推崇莱辛的的文学作品呈现了「具有史诗般磅礡气势的女性经验,她以怀疑的精神、强烈的使命感、透视心性的灵视力量,审视分崩离析的现代文明。」莱辛的作品一直秉持着异议分子对社会主流的思想、观念、价值提出质疑与批评,在文学上的成就是独一无二的。长达六十年的写作生涯,几乎每年一部作品都去审视现代文明的缺失,可谓是最严苛的西方知识分子的良知之一。
莱辛一九八五年出版的《善良的恐怖分子》(The Good Terrorist),在书名就揭示了善恶并陈的人性,而由原初的「好」演变成后来的「恶」,其中心理转折过程的细微刻划,就像是将心中的深层意识活动用显微镜放大来看,对于培养读者观察省思的能力有独特的用心。三年后,她犀利的批判力,又在《第五个孩子》中展现,就像一把锋利的刀,探讨社会之恶的形成,在处理人性及社会的黑暗面更是锐利。选择儿童为恐惧的对象,与知名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经典名作《碧庐冤孽》(The Turn of the Screw)中,两个如天使般纯洁美丽的小孩被恶灵附身,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位作家的作品,出版时间相距九十年,但是都用了小孩做为探讨邪恶显现的缘起,因为他们都深深了解到,邪恶的根源要回溯到人类原初的起源。
《第五个孩子》讲的是有关迥异于常人的小孩班的故事,班有四位正常、健康的哥哥姊姊,因为班的出现,原本一个快乐幸福的家庭,开始分崩离析。班之所以造成家人恐惧,是因为班虽然是小孩,但却具有如原始人强大的野蛮力量,再加上他奇特的长相、狩猎的天性、异常的行为,造成家人的梦魇。但是莱辛刻意模煳班的本质,将他塑造成一个寓意丰富的象征,让读者对于所谓的「异类」重新思考。
●
为什么会有班的出现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家的起源找到蛛丝马迹。父亲大卫与母亲海莉第一次做爱的房间,莱辛形容它为「无边际的黑暗洞穴」(like a black cave that had no end),这句话将我们带回到洞穴人的原始场景,暗示父亲体内仍保有野蛮人的基因。
父子血脉相连的线索,在班要出生前,父亲大卫讲童话故事给四个小孩听时又再度浮现。故事中一个小女孩在魔法森林中迷路了,她走到水池边,看到水中突然出现一个女孩的脸,直直地看着她,不怀好意地笑,很不友善,似乎要伸出手来把她拖下水。这是一个简单的童话故事,我们在年幼时都会听到,但是简单几句话所塑造出来的恐怖氛围,让人不寒而慄,所以外祖母桃乐西迅速把故事做一个结束。但是,那不怀好意的笑容所透露出来的恶意,象征邪恶的力量,其中的喻意,预告了班的出生及其所导致的家庭灾难。当小孩追问那不怀好意的女孩是谁时,父亲只解释她只是突然显象(materialize),过去并不存在。那么,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班是否就是代表恶的力量?像池中邪恶的女孩,突然显象了吗?这个问题,值得好好思考。
班究竟是何生物?有许多的说法,像邪恶小精灵、侏儒、丑陋矮小低能儿,但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些名词都有邪恶的含意,但班是否邪恶?从母亲海莉近距离的观察,读者得到的讯息,是班「好像有恶意」、「似乎有敌意」、「看起来邪恶」,但是直到故事结束,我们都无法断定班的本质是邪恶的。
不过,班那种无法控制的蛮力,及对比其他小孩的巨大差异,让父亲、祖父母坚决认定班是威胁正常生活和谐的异类,不能放在家中,于是他们联手安排,将班送进专门收容被弃养异常小孩的机构。他们明知在收容的机构里,班将受到残酷手段的控制,但仍然不顾亲子之情,送他过去,父亲大卫甚至否定了他们父子的连结。
在要送走班时,母亲海莉请求大卫,说他只是孩子,不要送走他们的孩子,他残忍地回答,「他当然不是我的孩子。」这是莱辛小说中对社会文明的人文关怀,观察人性能够包容及接纳异己的界线。当我们看到「正常人」为了维护和谐秩序,而用来处理班的手段之残酷不仁,这究竟是「异类」邪恶,还是「正常人」邪恶,也就不言而喻了。
●
莱辛曾说过,一个社会面对「异类」所做的抉择,是决定这个文明往上提升或向下沉沦的指标。这家人的姓是Lovatt,代表love爱,但是在面对班时,都不愿意去了解、包容班这个怪物,希望用最快的方式把妨碍家庭和谐的班除去,这是向下沉沦。
母亲海莉无法接受这种非人道的处理方式,当她看到收容所如地狱般的景象时,痛心班所经历的非人待遇,因此不顾家人的反对接回班,专心照顾、教育班,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适应社会。海莉因此而被家人孤立,认为她是破坏家庭的罪人。但是不管来自环境的反对力量有多大,也不管她为保护班不受伤害所付出的代价,海莉坚持她所认为应该遵循的人道原则─文明的社会不能因差异而岐视、打压、迫害异己,对待即使是看起来像是危险的野蛮人,也是一样。
因为班破坏了家的幸福生活,大卫视班为敌人,将他弃养;对比母亲海莉的救援、照顾及包容,此小说清楚地指出,唯有以爱与包容,才能够对于非我族类的他者,发出悲悯之心,以人道方式对待。
莱辛以其透视心性的洞察力,写出一部部作品,描述异议者、失败者、边缘人及畸零人的悲剧命运,一而再、再而三地检视了西方先进文明视野的狭隘与不足。但是莱辛小说所提供读者的,不仅仅是各种灾难与悲剧,隐藏在莱辛犀利的批判笔锋之下,是对于人类未来命运强烈的使命感,提醒我们应重新思考社会传统规范的价值,并点出提升人性及文明层次所应努力的方向。
就如诺贝尔评审团所肯定莱辛作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从崩坏与混乱浮现出的基本价值,让莱辛得以保留人类的希望。」在《第五个孩子》故事中,我们在这位平凡的母亲身上,看到莱辛为人类所保留的希望。海莉的故事,是人性在黑暗的时代、恶质的社会环境中挣扎奋斗的心路历程,她学习在恶劣的环境中,如何能够保持人类的希望及人性的光辉。
你想勒索爱情、勒索母爱,整个社会都会来帮助你
卢郁佳(作家)
芭芭拉.金索沃的小说《毒木圣经》(The Poisonwood Bible)描述比利时白人传教士家庭设法教化刚果殖民地黑人,文化鸿沟的悲剧。当中冷眼观察全局的女儿艾达,真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名英军因伤致残,娶了在医院结识的英国护士,战后在今天伊朗的英国帝国银行工作,生下莱辛。风闻许多人种玉米致富,他们全家搬到非洲的英属殖民地罗德西亚(今天的辛巴威)种玉米,却歉收贫穷,父亲无法适应当地。母亲则想教化黑人,当然也要把莱辛变成淑女,送她进天主教女校,听修女满口地狱恐吓学生。莱辛十三岁眼疾辍学,阅读伦敦寄来的小说自娱:狄更斯,沃尔特.史考特的浪漫冒险故事,史蒂文生《金银岛》,吉卜林,D.H.劳伦斯,斯汤达尔,托尔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她十五岁离家当保姆,读遍雇主政治、社会学书籍,跟雇主的姊夫上床,开始写小说发表在南非杂志上。当过电话接线员、速记员等,她说像地狱般孤独。十九岁嫁人,生下一子一女,私奔离婚。二战时在左翼读书会加入了南罗得西亚共产党,嫁给德国难民,然后离婚带着幼子移英国。穷得行李只有小说《青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的稿子,写一桩黑人男仆杀白人主妇的命案,以殖民地种族真相震动英国,一书成名,后来被南非和罗德西亚列为黑名单禁止入境。她加入英国共产党,后来因为苏联镇压匈牙利而退党。
莱辛此刻能出现在读者面前,绝不是来给体制锦上添花,是杀出血路、闯过地狱来的战神。她是文学上的暴民,与维吉尼亚.吴尔芙和西蒙.波娃并肩站在抗议队伍第一排。生为女人等于在殖民地做个黑人,但是,很少人愿意承认。莱辛《一封未投邮的情书》(An Unposted Love Letter)里的〈十九号房〉描述一对男女结了婚,妻子抛弃事业,实现家庭美梦,在郊区买大屋,生下一群孩子,被育儿和家务摧磨辗压。她设法适应,所有女人不都这么习惯了吗?她去了小旅馆开房,每早十点到下午五点窝在藤椅上放空。但是,她还得向丈夫伸手要钱付给旅馆。丈夫起了疑心,她为保住净土,谎称外遇,压力步步进逼。结局是她在旅馆房间开瓦斯自杀。
莱辛写女性经验,力道像空袭轰炸读者。在砲弹落下的当场,你会先听到一种震耳欲聋的寂静,像是世界空了。过去以后好像环境没有改变,然而身边的砖瓦却无故粉碎,如雨纷落,梁柱崩塌,撕开头顶屏障,裸出蓝天。原本读者置身于看似和谐的社会关系,但从翻开莱辛起,这种和谐维稳再也没有读者的立足之地。
《第五个孩子》在精采情节下就暗藏了颠覆世界的力量。这次出版,正值台湾社会透过《背离亲缘》(Far From the Tree)、《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情绪勒索》等畅销书集体审视原生家庭的伤害,我感激有生之年我终于成长到足以明白莱辛的讯息。读第一遍,这是个天真夫妻遭遇不幸的故事──第五个孩子出生就有暴力倾向,智能不足,像苹果日报「人间异语」。莱辛冷静的口吻令人感到类似公平的事物,轮流呈现每个角色的逻辑、喜恶,不扭曲,没有邪恶,悲剧只是命运无常。
读第二遍,瞬间房里所有盖在家具上的白布都掀开了──结局以后见之明迅速放大角色的颟顸,和他们拒绝面对的真相。极限揭露人隐而未显的本质,在这种X光射线照耀下,角色变形了,变得粗重庞大,他们的身躯像高楼投下阴影,笼罩读者;话声变得遥远尖锐,像是从浴缸水底下听客厅传来吼叫。莱辛的反讽笔触,像是让读者接手、凑上高倍望远镜,看角色说话时鼻头的痘疤怎样随着怒气发红,看见他的鼻毛怎样随着唿吸戳颤,甚至望远镜还变成大肠镜,一路看进肠壁。
小说把一层层的布花瓣叠起来,从中央一针戳透收紧,平面就辐射绽开球形花朵。布片就是「派对」这个群众之眼:最初邂逅的公司派对,呈现男女主角和外界互贴的标签。然后,每年过节一批亲戚来住上两週见证大家庭温暖幸福,亲戚和夫妻俩互贴标签。最后,欢乐派对变成海莉面对体制权威,求助医师、儿子校长召见她兴师问罪。海莉和特殊儿子班的独处互动,实际由背后这一层层互动所形塑。拉紧层瓣的缝线,就是别人怎么看夫妻俩。从外界观感产生的自我形象,成为主角斡旋的战场。海莉不断和这些扯她后腿的痛苦自我形象搏斗,从派对开始一路寻求认可,到认清她所要的只是对方承认问题,和她一起分担,这就是震动天地的女性成长。
●
小说展示的重点并非要不要生,而是众人如何做这个决定。两人想要很多孩子,至少六个。是谁想要?开头蓄意模煳,说两人都想要。接着更暧昧,「要不要继续生孩子」的问题,竟是通过「过节要不要邀请大批亲戚来家里住」的问题提出来探讨,而变成「哪些人必须出钱出力养孩子」,变成「要不要把班送走」。决定要不要生,像决定要不要邀亲戚过节,海莉无法说出要求,而以「不办宴会,孩子会失望」、「医生说班很正常」暧昧表达。海莉无权为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作主。
小说前半写海莉一意孤行多产,享受孕妇像女王受宠。众人怪海莉任性,没人把矛头指向大卫。后来海莉违逆大卫,坚持要生,大卫忍怒不发。海莉生下特殊儿,要求再多生几个。大卫的反应揭露了「生很多孩子」是大卫的期待。两人一见钟情,是海莉从雅房分租逃进大卫的小屋同居,而不是相反,说明了两人的权力关系。大卫不满双亲离婚后忽略他,决心以组织家庭修正自己的童年悲剧,「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女人。」「他的妻子在这方面必须像他:她必须知道快乐在哪里,该怎样维护。」莱辛用「什么」、「哪里」这幅无所不在的白布,遮住了大卫对海莉的爱情进行勒索的事实。大卫描述安全感的方式,是他少时的房间,这房间要他无止境扩充,大房子只是无穷饥渴在现实中有限的投影。
如果我们有权自主做决定,也就有权更改这决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改变心意。海莉虔诚追随大卫主导,最后跟丢了,像受难圣徒般死守任务,甚至为此反抗大卫。婚姻成了一场双人羽织表演,看起来是一个人在吃东西;羽织底下却是两个人,海莉的双手盲目在餵大卫,大卫说够了,但海莉继续。因为开头饿的人是大卫,所以进食无关海莉饿不饿。即使大卫饱了,海莉也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难以接受。因为海莉仍然饥饿,双人羽织从没餵进海莉的嘴。
两人生孩子,不是伴侣之爱扩及爱孩子,而是向父母讨爱。第一,大卫无法接受父亲施惠,只有借口养儿装作勉为其难接受。海莉母亲照顾唐氏症外孙女、外孙,代替亲近女儿,三个女儿也以争夺母亲顾孙来争夺母爱。这种爱就算讨到了,也不会饱,因为当事人不知道自己在讨什么,也不觉得被爱。第二,大卫无法亲近任何人。他跟海莉相处轻松,因为自从第一胎出生后,夫妻就没有单独共处过。生孩子免除了他面对妻子的折磨,掩盖了问题,让海莉饿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在挨饿。情感交流像洗钱般不停转换名目,结果都在孤立海莉。
孩子遇到问题,整个社会都推给母亲海莉,要她负责解决。但海莉得从小有母亲支持,才能抗衡大卫。得有大卫合作,才能抗衡特教体制。抽掉这两个心理资源支柱,海莉就被困境压死。社会诉诸母爱应该解决一切,就是对母爱进行勒索。
●
来自非洲热烈荒野的莱辛,向晚披襟眺望席卷资本主义社会的情感匮乏冰风,写下如此悲切之笔:
海莉想婚后先工作两年存钱再生,但因大卫坚持而怀孕。大卫「放肆、毫无忌惮的大笑,完全不像平常那个谦沖、知趣、得体的大卫」,笑容里的祕密隔绝了海莉,使她不安。这是大卫的真正面貌,只因压抑而沦为施虐。
「孩子们的原始野性,前一刻还在他们的血液里跳动;但现在必须把原始狂野的一面放下,才能够重新回归家庭。」海莉与大卫「两个成年人坐在那里,温顺,居家,甚至可怜,因为野性和自由早就离他们远去」。
海莉求助于女医生吉利,医生归罪她搪塞,然后「突然、出乎意料地,毫不掩饰地透露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她是个端庄的中年妇人,她的人生充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在这一个瞬间,一股不受控、不合法理的忧虑显露了出来」。
职场,家庭,生活,台湾的我们正在经历情感的冰河期,女人被爱勒索的酷烈时代。《第五个孩子》说出了人们只能模煳感觉的事,只能在梦中一瞥随即遗忘的真相。
因为我们需要莱辛,所以莱辛在这里。
恶何以形塑?
杨薇云(元智大学应用外语系、淡江大学英文系兼任副教授)
恶为何会出现?什么时候出现?经由什么样的原因,形塑成形,造成伤害死亡,社会秩序的崩解?这问题,从古至今困扰了不知多少领导者、宗教家、道德家、哲学家、心理学家、法律人。最近刚刚落幕的公视年度大戏《我们与恶的距离》,促使台湾无数的观众共同省思: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与恶的距离有多近?
恶这个最难捕捉的人性元素,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的《第五个孩子》故事中,有着非常细腻的描述与诠释,看过《与恶》的观众们,绝不可错过这部精准刻划出边缘人的极品。阅读此书,读者可以欣赏莱辛精简犀利透澈的文字,体会到边缘人在正常人的敌视中,孤独生活的痛苦,也可看到社会文明的主流力量,为了维护正常的生活,不惜除去一个异常小孩的残酷。人与恶的距离,很难评断,但是在文明道德价值混乱的时代,维护人道的底线,为主角奋斗的目标,也是读者关切的重点。
●
二○○七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颁赠诺贝尔文学奖给八十八岁的莱辛,委员们推崇莱辛的的文学作品呈现了「具有史诗般磅礡气势的女性经验,她以怀疑的精神、强烈的使命感、透视心性的灵视力量,审视分崩离析的现代文明。」莱辛的作品一直秉持着异议分子对社会主流的思想、观念、价值提出质疑与批评,在文学上的成就是独一无二的。长达六十年的写作生涯,几乎每年一部作品都去审视现代文明的缺失,可谓是最严苛的西方知识分子的良知之一。
莱辛一九八五年出版的《善良的恐怖分子》(The Good Terrorist),在书名就揭示了善恶并陈的人性,而由原初的「好」演变成后来的「恶」,其中心理转折过程的细微刻划,就像是将心中的深层意识活动用显微镜放大来看,对于培养读者观察省思的能力有独特的用心。三年后,她犀利的批判力,又在《第五个孩子》中展现,就像一把锋利的刀,探讨社会之恶的形成,在处理人性及社会的黑暗面更是锐利。选择儿童为恐惧的对象,与知名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经典名作《碧庐冤孽》(The Turn of the Screw)中,两个如天使般纯洁美丽的小孩被恶灵附身,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位作家的作品,出版时间相距九十年,但是都用了小孩做为探讨邪恶显现的缘起,因为他们都深深了解到,邪恶的根源要回溯到人类原初的起源。
《第五个孩子》讲的是有关迥异于常人的小孩班的故事,班有四位正常、健康的哥哥姊姊,因为班的出现,原本一个快乐幸福的家庭,开始分崩离析。班之所以造成家人恐惧,是因为班虽然是小孩,但却具有如原始人强大的野蛮力量,再加上他奇特的长相、狩猎的天性、异常的行为,造成家人的梦魇。但是莱辛刻意模煳班的本质,将他塑造成一个寓意丰富的象征,让读者对于所谓的「异类」重新思考。
●
为什么会有班的出现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家的起源找到蛛丝马迹。父亲大卫与母亲海莉第一次做爱的房间,莱辛形容它为「无边际的黑暗洞穴」(like a black cave that had no end),这句话将我们带回到洞穴人的原始场景,暗示父亲体内仍保有野蛮人的基因。
父子血脉相连的线索,在班要出生前,父亲大卫讲童话故事给四个小孩听时又再度浮现。故事中一个小女孩在魔法森林中迷路了,她走到水池边,看到水中突然出现一个女孩的脸,直直地看着她,不怀好意地笑,很不友善,似乎要伸出手来把她拖下水。这是一个简单的童话故事,我们在年幼时都会听到,但是简单几句话所塑造出来的恐怖氛围,让人不寒而慄,所以外祖母桃乐西迅速把故事做一个结束。但是,那不怀好意的笑容所透露出来的恶意,象征邪恶的力量,其中的喻意,预告了班的出生及其所导致的家庭灾难。当小孩追问那不怀好意的女孩是谁时,父亲只解释她只是突然显象(materialize),过去并不存在。那么,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班是否就是代表恶的力量?像池中邪恶的女孩,突然显象了吗?这个问题,值得好好思考。
班究竟是何生物?有许多的说法,像邪恶小精灵、侏儒、丑陋矮小低能儿,但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些名词都有邪恶的含意,但班是否邪恶?从母亲海莉近距离的观察,读者得到的讯息,是班「好像有恶意」、「似乎有敌意」、「看起来邪恶」,但是直到故事结束,我们都无法断定班的本质是邪恶的。
不过,班那种无法控制的蛮力,及对比其他小孩的巨大差异,让父亲、祖父母坚决认定班是威胁正常生活和谐的异类,不能放在家中,于是他们联手安排,将班送进专门收容被弃养异常小孩的机构。他们明知在收容的机构里,班将受到残酷手段的控制,但仍然不顾亲子之情,送他过去,父亲大卫甚至否定了他们父子的连结。
在要送走班时,母亲海莉请求大卫,说他只是孩子,不要送走他们的孩子,他残忍地回答,「他当然不是我的孩子。」这是莱辛小说中对社会文明的人文关怀,观察人性能够包容及接纳异己的界线。当我们看到「正常人」为了维护和谐秩序,而用来处理班的手段之残酷不仁,这究竟是「异类」邪恶,还是「正常人」邪恶,也就不言而喻了。
●
莱辛曾说过,一个社会面对「异类」所做的抉择,是决定这个文明往上提升或向下沉沦的指标。这家人的姓是Lovatt,代表love爱,但是在面对班时,都不愿意去了解、包容班这个怪物,希望用最快的方式把妨碍家庭和谐的班除去,这是向下沉沦。
母亲海莉无法接受这种非人道的处理方式,当她看到收容所如地狱般的景象时,痛心班所经历的非人待遇,因此不顾家人的反对接回班,专心照顾、教育班,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适应社会。海莉因此而被家人孤立,认为她是破坏家庭的罪人。但是不管来自环境的反对力量有多大,也不管她为保护班不受伤害所付出的代价,海莉坚持她所认为应该遵循的人道原则─文明的社会不能因差异而岐视、打压、迫害异己,对待即使是看起来像是危险的野蛮人,也是一样。
因为班破坏了家的幸福生活,大卫视班为敌人,将他弃养;对比母亲海莉的救援、照顾及包容,此小说清楚地指出,唯有以爱与包容,才能够对于非我族类的他者,发出悲悯之心,以人道方式对待。
莱辛以其透视心性的洞察力,写出一部部作品,描述异议者、失败者、边缘人及畸零人的悲剧命运,一而再、再而三地检视了西方先进文明视野的狭隘与不足。但是莱辛小说所提供读者的,不仅仅是各种灾难与悲剧,隐藏在莱辛犀利的批判笔锋之下,是对于人类未来命运强烈的使命感,提醒我们应重新思考社会传统规范的价值,并点出提升人性及文明层次所应努力的方向。
就如诺贝尔评审团所肯定莱辛作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从崩坏与混乱浮现出的基本价值,让莱辛得以保留人类的希望。」在《第五个孩子》故事中,我们在这位平凡的母亲身上,看到莱辛为人类所保留的希望。海莉的故事,是人性在黑暗的时代、恶质的社会环境中挣扎奋斗的心路历程,她学习在恶劣的环境中,如何能够保持人类的希望及人性的光辉。
图书试读
……
时光匆匆。时光的确匆匆,只不过她被限制在与周遭人们不同的时间表里──也不同于一般孕妇,她们的时间是缓慢的,是一个隐藏的生命孕育成长的日程。而她的时光就是忍耐,包含着痛苦的忍耐。鬼魅和妖怪就住在她的脑子里。她想到科学家在做实验,把两个不同种类和体型的动物接合在一起,这大概就是她这种可怜母亲的感受了。她幻想着身体里就怀着这样可怜又笨拙的怪物,真切的可怕,是大丹或俄国牧羊犬和小哈巴狗的混种;是狮子和狗的混种;是拉车的大马和小毛驴的;是老虎和山羊的。有时她确信有动物的蹄子──有时是爪子──在割裂她体内柔软的血肉。
下午,她先去学校接两个孩子,再去车站接大卫。吃过晚餐,她总是在厨房里兜圈子,催促孩子们快去看电视,然后上三楼,在走廊上来回疾走。
全家人都能听见楼上传来她又快又重的脚步声,大家都不敢互相对视。
时光匆匆。时光的确匆匆。第七个月情况好多了,因为她服用了大量的镇静剂。这时她发觉她和丈夫、和孩子们、和母亲、和艾莉丝之间的隔阂愈来愈大,她惊骇极了。她决定做好一件事:每天从下午四点,海伦和路克放学后,到晚上八、九点,他们上床睡觉的这段时间里,让自己看起来还算正常。镇静剂对她产生的影响不大,她凭着意志力不让药剂干扰到她自己,只许接触胎儿──这个叫她吃尽苦头的怪物。在这几小时里它都很安静,万一有醒来的迹象,或又开始打她,就再吃药。
啊,大家多么渴望她回归正常、多么欢迎她回归家庭:他们不知道的是──她刻意不要他们知道──她的紧张,她的累。
大卫会搂着她说:「啊,海莉,妳真的没事?」
还剩两个月。
「是啊是啊,我没事。真的。」她默默地对蜷缩在她子宫里的怪物说,「你现在给我乖乖的,否则我就再吃一颗药。」似乎它真的在听,而且听懂了。
时光匆匆。时光的确匆匆,只不过她被限制在与周遭人们不同的时间表里──也不同于一般孕妇,她们的时间是缓慢的,是一个隐藏的生命孕育成长的日程。而她的时光就是忍耐,包含着痛苦的忍耐。鬼魅和妖怪就住在她的脑子里。她想到科学家在做实验,把两个不同种类和体型的动物接合在一起,这大概就是她这种可怜母亲的感受了。她幻想着身体里就怀着这样可怜又笨拙的怪物,真切的可怕,是大丹或俄国牧羊犬和小哈巴狗的混种;是狮子和狗的混种;是拉车的大马和小毛驴的;是老虎和山羊的。有时她确信有动物的蹄子──有时是爪子──在割裂她体内柔软的血肉。
下午,她先去学校接两个孩子,再去车站接大卫。吃过晚餐,她总是在厨房里兜圈子,催促孩子们快去看电视,然后上三楼,在走廊上来回疾走。
全家人都能听见楼上传来她又快又重的脚步声,大家都不敢互相对视。
时光匆匆。时光的确匆匆。第七个月情况好多了,因为她服用了大量的镇静剂。这时她发觉她和丈夫、和孩子们、和母亲、和艾莉丝之间的隔阂愈来愈大,她惊骇极了。她决定做好一件事:每天从下午四点,海伦和路克放学后,到晚上八、九点,他们上床睡觉的这段时间里,让自己看起来还算正常。镇静剂对她产生的影响不大,她凭着意志力不让药剂干扰到她自己,只许接触胎儿──这个叫她吃尽苦头的怪物。在这几小时里它都很安静,万一有醒来的迹象,或又开始打她,就再吃药。
啊,大家多么渴望她回归正常、多么欢迎她回归家庭:他们不知道的是──她刻意不要他们知道──她的紧张,她的累。
大卫会搂着她说:「啊,海莉,妳真的没事?」
还剩两个月。
「是啊是啊,我没事。真的。」她默默地对蜷缩在她子宫里的怪物说,「你现在给我乖乖的,否则我就再吃一颗药。」似乎它真的在听,而且听懂了。
用户评价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