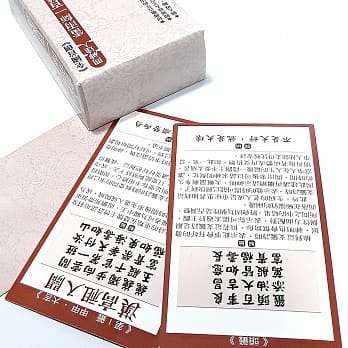具体描述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2018年1月,在财团法人台南市台疆祖庙大观音亭暨祀典兴济宫运筹帷幄下,「世界保生大帝庙宇联合总会」于台南正式成立,世界各地参与之宫庙多达三百多家,盛况空前。
为了宏扬保生大帝慈济爱民的精神,祀典兴济宫2018年10月又与国立成功大学、国立金门大学、闽南师范大学、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漳州市闽南文化研究会、漳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等单位,在台南-金门-漳州三个地方,合作接力举办「世界保生大帝信仰学术研讨会」,邀请法国、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中国大陆和台湾等超过七十位国内外学者专家与会,共发表四场主题演讲和三十篇最新研究论文,而且这还不包括漳州场参会的另外八篇文章。
2018「世界保生大帝信仰学术研讨会」横跨海崃两岸三地的办会方式,其难度之高,令海内外学者齐声赞叹。又由于「世界保生大帝庙宇联合总会」所聘四位学术总顾问(王秋桂教授、李丰楙教授、林从一副校长、黄奇校长),以及台湾、厦门、漳州、泉州众多有关宫庙代表的热情参与,其成果之丰硕也获得各界一致的肯定。
如今,有二篇主题演讲稿,和通过严格学术审查并经作者仔细修订的二十五篇学术论文,涵盖台湾与金门保生大帝信仰、福建与香港保生大帝信仰、日韩与东南亚保生大帝信仰,共同结集成这部掷地有声的《台湾与各地之保生大帝信仰研究》,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应该感谢的单位与个人非常多,请恕我不一一列举。不过,有一位我不得不提,那就是台南进士汪春源曾孙、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客座教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汪毅夫先生,他在「世界保生大帝信仰学术研讨会」漳州场,做了名为〈重读《兴济宫题联并记》〉的特别发言:
我多次到过台南祀典兴济宫,每次都会看到台湾知府周懋琦的题联和题记。五年前,我在兴济宫演讲时,用闽南语说:「周懋琦是一个足有才调的人,伊写的对联是兴济宫的一件宝物。伊写的上联『秉笔陋元臣医药神灵宋史漏收方伎传』是对《宋史》的批评:《宋史》的『秉笔』人即执笔者忽略了宋代的两位『元臣』即宰相曾怀和钱象祖,《宋史》之〈方伎传〉还漏收了『医药神灵』的吴夲,另一方面则是对吴夲生前作为神医的推崇;下联『熙朝修祀典馨香朔望清时合祭观音亭』说的是盛明之朝(熙朝),吴夲身后作为医神保生大帝配享百姓遵循祀典(吴夲作为医神载在祀典始于宋干道二年即1166年),朔望拈香致祭,清平之世(清时)兴济宫与观音亭合为同一祭祀圈也。」我当时还推测说,联之题记所谓「神生于宋太平兴国四年,姓吴,与龙图阁待制番阳熊伯通仝名」是用曲笔或者说春秋笔法,利用通假字(于、于,仝、同,夲、本)的使用原则,批评《宋史》 之〈熊本传〉将宋「龙图阁待制熊伯通」之名(夲)误为「本」。
今日重读周懋琦〈兴济宫题联并记〉,我首先要为「《宋史》之〈熊本传〉将宋『龙图阁待制熊伯通』之名(夲)误为『本』」的推测提供一个「刻在石头上的证据」。经众多学界友人的指导和协助,我得到江西省景德镇陶瓷民俗博物馆收藏的宋碑〈宋故宝文阁待制程公墓志铭〉之碑体照片和拓本照片,墓志铭提及「龙图阁待制熊公伯通」的名讳均作「夲」。周懋琦既说保生大帝吴夲与熊伯通同名,则熊伯通的名讳当然是「夲」。然而「孤证不为定说」,我的推测尚待实也。
周懋琦对联题记里有关于保生大帝在台湾的功德。「同光戌亥间」即同治甲戌(1874)至光绪乙亥(1875),周懋琦参与沈葆祯主导的「开山抚番」之役。由于时疫流行,官兵疫死者众。沈葆祯等向保生大帝「竭诚祈请疫不为厉」,幸未蔓延为瘟疫。周懋琦为兴济宫题联,为的正是对医神保生大帝念其德、报其功。作为医神信仰,保生大帝信仰以富有正能量的防疫减灾、施药活病乃至济困、助学的公益活动为其特色。
附带言之,周懋琦编着的《全台图说》有关于钓鱼岛的记载,略谓:「山后大洋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余艘」。
汪毅夫先生这次的发言,是针对他在2013年「祀典兴济宫暨保生大帝信仰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演讲〈千年祀典俎豆馨香--读周懋琦《兴济宫题联并记》〉的后续补充,可见他与台南市大观音亭暨祀典兴济宫渊源之深,情意之切,令人感动。
《台湾与各地之保生大帝信仰研究》出版在即,我在想,祀典兴济宫2018年能够克服万难,把保生大帝信仰研究带出台南走向金门和漳州,那么台疆祖庙大观音亭2019年是不是也可以将观音信仰研究带出台湾走向观音信仰日益蓬勃的越南呢?这个想法倘能实现,那么这又会是财团法人台南市台疆祖庙大观音亭暨祀典兴济宫与国立成功大学、国立金门大学再一次令人惊艳的合作壮举了。
陈益源2019.4.15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我一直对神祇信仰的“跨地域”传播及其在地化过程充满好奇。当看到《台湾与各地保生大帝之信仰研究》这个标题时,我立刻联想到,许多源自大陆的民间信仰,在传入台湾后,往往会因为新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和文化交流,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我特别希望这本书能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审视保生大帝信仰是如何从其原乡,如福建,一步步传播到台湾,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吸收了哪些当地的文化元素,又与哪些台湾本土的神祇信仰产生了有趣的互动。我设想书中可能包含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保生大帝宫庙的比较分析,例如,分析台湾的保生大帝庙宇在建筑风格、祭祀仪式、神诞活动等方面,是否与大陆沿海地区的原乡庙宇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我也希望作者能够深入探讨保生大帝的“行医济世”形象在台湾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这一形象如何影响了台湾民间医疗观念和实践。研究保生大帝信仰的传播,不仅仅是追溯一个神祇的足迹,更重要的是理解移民文化在异域的扎根与变迁,以及信仰如何成为构建和维系社群的重要纽带。我期待书中能够提供丰富的案例,展现保生大帝信仰在台湾社会的各个层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评分我对神明信仰的地域性演变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当一个在原乡根深蒂固的信仰,移植到新的地域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异和发展。《台湾与各地保生大帝之信仰研究》这个书名,恰恰点出了我想要探究的核心问题。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够详细地解析保生大帝信仰在台湾的传播路径,以及它如何在台湾的土地上,与原有的文化土壤相结合,孕育出独特的信仰实践。例如,在台湾的各个县市,保生大帝的祭祀方式、神诞庆祝活动、以及信众的祈求内容,是否会因为地理、族群、历史背景的不同而产生显著差异?我渴望看到书中能够呈现一些具体的宫庙案例,分析这些宫庙在历史发展中,如何适应台湾的社会变迁,并不断调整其信仰内涵和功能。同时,我也对保生大帝信仰如何融入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它在医疗、社区建设、甚至地方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抱有极大的探究欲望。如果书中能够通过翔实的田野考察和对地方文献的深入解读,描绘出保生大帝信仰在台湾的生动图景,那将是一次极具价值的阅读体验。
评分作为一名长期关注民间宗教研究的学者,我对《台湾与各地保生大帝之信仰研究》的潜在内容感到非常兴奋。我尤其关心的是,这本书是否能够提供一个比较性的视角,来审视保生大帝信仰在台湾与在福建原乡,乃至其他海外华人社区的发展差异。例如,在福建,保生大帝可能更多地与地方士绅、宗族势力紧密相连;而在台湾,随着历史进程和不同族群的迁徙,保生大帝的形象和功能是否有所演变,比如更加侧重于医疗救赎,或者与某些社会经济活动产生更强的联系?我希望书中能够深入探讨保生大帝信仰在台湾落地生根的过程中,是如何与其他本土的神祇信仰,如王爷、妈祖等,发生融合或竞争,从而形成独特的台湾民间信仰体系。此外,我也期待书中能够关注保生大帝信仰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传播,以及其在现代社会中依然保持活力的原因。一个成功的民间信仰研究,往往需要结合历史文献、考古资料以及田野调查,从宏观的文化背景到微观的个体经验,全方位地展现信仰的生命力。我对这本书能否在这些方面提供深入的分析和扎实的论证,充满了期待。
评分我一直在寻找能够深入解读中国民间神祇信仰在地域间传播的书籍,尤其是那种能够细致剖析神祇形象、祭祀仪式以及信仰社群在不同文化语境下变迁的著作。《台湾与各地保生大帝之信仰研究》这个书名,让我立刻联想到,保生大帝作为一位重要的民间医神,其信仰在从福建沿海传播到台湾的过程中,必然会经历一系列的在地化过程。我非常希望这本书能够详细探讨保生大帝在台湾的信仰源流,以及它如何与台湾本土的宗教文化、社会结构相融合。我期待书中能够呈现出,保生大帝在台湾的形象是否有所演变,例如,在祭祀活动中是否增添了新的元素,或者其“救世济民”的神格在台湾民众心中是否有了更具体的体现。此外,我也对保生大帝信仰如何成为凝聚台湾社区、维系宗族关系,甚至影响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充满好奇。如果书中能够提供扎实的田野调查资料,包括对不同地区保生大帝宫庙的考察,以及对信众的访谈,那将极大地增强其学术价值和可读性。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更深刻地理解民间信仰是如何在新的环境中生根发芽,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评分作为一名对中国民间信仰,尤其是妈祖以外的神祇研究颇感兴趣的读者,我一直试图寻找能够深入探讨特定地方神祇信仰的书籍。《台湾与各地保生大帝之信仰研究》这个书名,立刻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从书名来看,我期待它能详尽地梳理保生大帝在台湾的传播历程,并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地理视野中进行比较。我尤其希望书中能够呈现保生大帝信仰在不同地区,如福建泉州、漳州,乃至其他海外华人聚居地的演变和发展,分析其在不同地域文化语境下的在地化特色。例如,保生大帝在台湾的信仰形态,是否与他在福建原乡的祭祀方式有所差异?又或是,随着移民的迁徙,保生大帝的职能和形象是否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变化?我希望能看到作者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呈现出这些鲜活的细节。此外,书中对保生大帝信仰的社会功能,如如何成为凝聚社区认同、维系宗族关系、甚至影响地方政治格局的工具,也会是我非常关注的部分。如果书中能加入一些具体的个案研究,比如某个宫庙的历史演变,或是某个家族对保生大帝的特殊情感连接,那将极大地增强其可读性和学术价值。我一直相信,真正的信仰研究,离不开对普通信徒生活经验的细致描摹,以及对信仰在日常生活中扮演角色的深刻理解。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