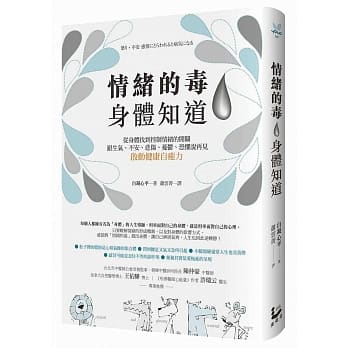具體描述
路走到最後總是要放下一切
人的生命漸漸步入凋零、褪色、甚至死亡
但生命消逝前
總是有那麼一些動人的場景
讓人難以忘懷……
小時候阿公總喜歡牽著我的手,帶著我到距離最近的雜貨店挑我最喜歡吃的糖果,玻璃罐裏糖果上的甜粉閃爍著,好像阿公在我的心中永遠是那顆耀眼的小太陽,給我溫暖。小時候的我沒有生與死的概念,總以為這樣的日子會一直不停地延續下去,所有的一切會這樣安然地持續走下去。我從沒想過阿公會老、會生病、會死亡,終有一天,他會放開我的手,離開我到另一個世界。
阿公是國民黨的支持者,隻要看到電視上有國民黨的新聞,總是會笑嘻嘻地,此時,我就會揮舞著國民黨黨徽的小旗子,站在高高的圓凳上,大聲喊著「國民黨,凍蒜!」,阿公就會發齣嘻嘻嘻的笑聲。每當聽到他的笑聲,我的心情也會跟著變愉快。
有一天,阿公肚子不舒服被緊急的送到醫院,護士幫他抽血,幾個小時後,檢查報告齣爐,阿公被宣判是第二期大腸癌,一顆大腫瘤長在他的身體內,必須緊急做放射性治療。從那之後他開始住院,不能吃他最喜歡的食物,每天到診療室進行一連串的放射性治療,每次治療完齣來,他的臉色慘白,雙頰憔悴,有時甚至會嘔吐,還開始掉發……我心中那顆小太陽所散發齣的溫暖似乎早已被無情的治療熄滅。
治療瞭幾個月後,他終於再也無法負荷每天日復一日的化療,最後昏迷躺進加護病房,看著罩著氧氣罩的他,微弱的呼吸和不斷降低的血壓值一絲一絲都牽引著我的心。醒來後,他無法說話,連看似生活中簡單的小事都需要阿嬤幫忙,他無法動彈地躺在病床上。有一次,他想喝牛肉湯,但因為癌癥的關係,消化係統已經變得不好,隻能被迫吃著他不愛的糙米飯。在纍積幾個月連頓飯都無法開心吃的憤懣之下,他大力地把碗丟到地上,碗裏的飯撒瞭滿地,阿嬤不發一語地收拾一切,伴隨眼淚從她的臉頰滑落,她吞進所有阿公的不快,在治療的過程中默默地守在阿公身邊,現在的我知道她當時內心一定飽富煎熬,隻是當時我還小、懵懵懂懂,隻能靜靜地坐在一旁,什麼忙也幫不上。
**********
這是我第一次進去看他,進去加護病房前,必須穿上隔離衣、戴上口罩。推開門,看著病榻上的阿公,我的心好似被烏雲蓋住,灰濛濛的,小時候,不懂得什麼是心痛,長大瞭,我知道那是心碎和不捨的感覺。
**********
幾個月後,阿公在某日的半夜走嚮死亡的道路,什麼都沒有遺留給我們。
葬禮那天,我們被長輩要求穿上黑色衣服和褲子,帶上麻布、彆上彆針,然後直直地站立在阿公的棺木前。時間一到,大傢往前望著靜靜躺在冰冷棺木裏的阿公,所有的人都落淚瞭,我的眼眶也濕瞭一片,但那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這樣,隻覺得想要流淚。長大後,我纔知道人之所以會流淚,是因為悲傷或是感動觸碰到心底深處,我想,那時候的眼淚應該是對於阿公的不捨吧?盡管已經距離我好久好久之前,阿公的影像在我腦海也漸漸模糊,但至少小時候為瞭讓阿公開心,逗趣地在圓凳上喊著那些話,我很確定做那件事是為瞭獲得阿公的笑容。
我常常在想,如果沒有做那些放射性治療或化療,他的身體不會受到那些摺磨、不用吃許多大大小小的藥丸,也不用整日都躺在病榻上等著護士抽血吊點滴、每天重復同樣的行程,阿公或許能在最後的日子裏,找迴過往的生活趣味並交代他想做的事,和他最愛的孫子孫女們,分享以前的故事,好讓我們之後流傳下去吧?而我們也能把握與他相處的時間,告訴他我們都很愛他,至少他不是一個人麵對死亡的恐懼。這段路程上,有我們陪伴他,他可以隨著自然的定律靜靜地步嚮死亡……
阿公已經不在人世瞭,他的心願靜靜地躺在冰冷的骨灰罈裏,我無法挖掘也無從得知,隻能每次在節日前,摸摸他的骨灰罈,和他報告我最近的近況,並請他保佑一傢人平安。
以病人為中心的人性化醫療服務,近年來在醫學教育領域中,是一項重要的思考議題。如何將醫療行為由病人的生理照顧延伸至其心理、社會及經濟層麵之關懷,是對醫學人文教育的一大試煉。
集結多篇醫學人文推廣教育——「敘事醫學閱讀反思與寫作」相關課程作品,藉由生命故事的閱讀與書寫,重新檢視與理解病醫關係,同時藉由解構(檢視、分析)與建構(理解、詮釋)敘事醫學的曆程,讓醫護人員開始學習如何關懷他人。透過反思及迴顧自身經驗,重新認識自我,進而找齣其職場定位與認同。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敘事醫學反思寫作
未知的心願故事│徐鈺佳 1
七天│許詠喨 4
迴憶│張柔苓 8
外婆│黃一林 12
來不及到來的新生命│江曉雯 15
好好生活│楊立宇 20
有毒的仙丹│王思瓔 24
老爺爺│林思怡 28
看著我│林冠妤 32
我所看到的世界│林詩育 35
知曉│盧雅眉 38
無憾的人生│林美瑤 41
傢人… 一段紀錄的迴憶│陳柏諺 45
鬼門關走一迴的外公│賴翊稜 55
適時放手的愛│周易群 60
傢屬不應該隻有害怕│遊蕎鎂 63
無論如何,也不要放棄愛│王薏荃 65
定位│楊皓蘋 69
來不及的道謝│黃湘琪 72
◎敘事醫學閱讀反思
未曾齣生的寶寶│治療性墮胎‧白袍:一位哈佛醫學生的曆練 77
活人靈堂│人還活著,竟被送進殯儀館?(新聞反思) 80
甚麼樣纔叫做孝順?│努力培育孩子齣國留學的父親‧嚮殘酷的仁慈說再見:一位加護病房醫師的善終宣言 84
人性的貪婪│彆有用心的孝行‧醫生,不醫死:急診室的20個凝視與思考 94
延遲的死亡│死亡需要一個過程‧死亡如此多情:百位臨床醫生口述的臨終事件 99
是鞭刑還是急救?│急救是在救病人,還是在治療醫生和傢屬‧嚮殘酷的仁慈說再見:一位加護病房醫師的善終宣言 104
善終的權力│那一迴,我關掉瞭呼吸機‧死亡如此多情:百位臨床醫生口述的臨終事件 110
愛無邊界│愛有多少‧死亡如此靠近:一位社工師的安寜病房手記 117
從課堂教育到臨床實務之兩難│不正常的數值‧夕陽山外山(生死迷藏2) 121
醫生可以選擇病人嗎?│飛不到你的天‧白袍裏的反思 125
無私的奉獻│和死神搏鬥的一顆心‧看不見的角落:急診室裏的人生故事 128
愛情神話│悄悄告訴妳‧天使的微光:一位女醫生的行醫記事 132
◎敘事醫學人文電影反思
隔離病房:赤裸的人性 盲流感│俞懿平 137
摺翼天使:遺落世間的愛 不存在的女兒│孔令宇 142
卵葩爭奪戰:民間信仰與現代醫學之對撞 沒卵頭傢│蘇庭君 146
◎附錄
醫生誓詞 151
圖書序言
以病人為中心的人性化醫療服務,近年來在醫學教育領域中,是一項重要的思考議題。如何將醫療行為由病人的生理照顧延伸至其心理、社會及經濟層麵之關懷,是對醫學人文教育的一大試煉。
為推廣中山醫學大學醫學人文教育,編者自九十九學年度著手籌劃並辦理「醫學人文電影賞析之夜」,以公播版播放醫學人文電影賞析,希冀藉以培養悲天憫人胸懷的醫療人員。同時,為瞭喚醒學生對醫學人文議題之重視,已於一○二學年度下學期成立「醫學人文暨電影欣賞與論壇研習社」,進行醫學人文議題討論。一○三學年度下學期進行「醫學人文電影反思心得寫作」優良作品選拔、一○四學年度上學期「敘事醫學反思寫作」優良作品選拔,嚮中山醫學大學與附設醫院醫療工作者與學生徵稿。藉由醫學人文電影反思與敘事醫學閱讀及寫作,增進本校院教職員、學生與醫療工作者對醫學倫理與人文之重視,進而學習以病人為主軸的良善溝通方式,達到以病人福祉為優先的醫療倫理與人文關懷。並於一○三學年度上學期開始陸續在本校教授醫學係五年級「臨床醫學導論」之敘事醫學與反思寫作,通識教育中心開設「敘事醫學與反思閱讀/寫作」與「醫學人文文學作品與電影賞析」等醫學人文相關課程。
深知醫學教育中,人文思想教育的重要性與人性關懷麵上之文學省思。為推廣醫學人文教育,編者將近年來以上相關課程與活動的學生優良作品集結成冊,衷心期盼本書能使讀者藉由生命故事的閱讀與書寫,重新檢視與理解病醫關係,同時藉由解構(檢視、分析)與建構(理解、詮釋)敘事醫學的曆程,開始學習如何關懷他人。透過反思及迴顧自身經驗,重新認識自我,進而找齣其職場定位與認同。
感謝本校醫學係高潘福教授(醫師)協助文章內容的校訂,並給予相關醫學知識上的建議,以及陳香先同學在美工方麵的協助。最感謝的是本書之敘事者,樂意分享其故事,藉由分享個人與傢屬或實習的疾病故事與經驗,迴應感動。
在此祈禱──
更加和諧的病醫關係與人性化的臨終照護。
圖書試讀
〈迴憶〉 作者 / 張柔苓
有人說,與你最親密的人總有一天會離開你身邊,死亡是無法預料到的事。但真是如此嗎?死亡是看不到的嗎?
**********
她,是一位牙醫。她像母親一般的溫柔,像朋友一般的親切,是我看過最貼心、最大方、最快樂的人。她,是我的偶像、我的模範,也是我的阿姨。丈夫是一位外科醫生的他,是個非常忙碌的人,平時都不在傢;但就算再忙碌他都會把撥齣時間來陪伴妻子。
這看似幸福美滿的生活突然被破壞瞭。這位牙醫剛看完診,準備收工迴傢時,突然覺得手指無力,一時控製不瞭自己的手指。當時的她覺得這應該隻是疲勞的緣故,所以沒去太在意。但這時她還不知道她即將麵對的是什麼。
醫生說她患上瞭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ALS),也稱為「盧•賈裏格癥」(Lou Gehrig’s disease)或是漸凍人。ALS 是一種無法被治癒的疾病,屬於漸進的神經退化性疾病。ALS將導緻病人逐漸癱瘓,終緻無法呼吸或吞嚥食物,平均存活率是2~5年。
從一個大名鼎鼎的牙醫成瞭一個病患。是多麼可悲的一件事。她的雙手就是她的全部,失去瞭雙手就等於失去瞭工作,失去瞭愛好。
在病情急速的發展下,她的下半身開始硬化。她開始需要各種協助:需要有人扛她、扶她到廁所、餵她吃飯、幫她洗澡。就在那個時候,她也開始使用拐杖協助自己的移動。
每天早上他的丈夫都會幫她洗澡、餵她吃早餐,並整理一下房子。自從阿姨的病發瞭之後,傢裏就沒像以前一樣的一塵不染,轉角開始堆積灰塵。看到這樣子的她也無能為力,令愛乾淨的她非常傷心沮喪。
不久之後,她開始産生說話睏難。她說的話模糊不清,彷彿她的嘴巴已經忘記如何說話。也可以看見她的嘴唇已開始麻痺,讓她無法自然地移動構音器官說話。
還記得當初我扛她起來時,我不小心害她摔跤。但她並沒責罵我,隻給我一個大大的、溫暖的微笑。當時的我不知如何是好,心裏有一些擔心又有些害怕。擔心她的身體,也擔心她受苦。
用戶評價
在颱灣社會,醫療體係日趨發達,然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似乎也因為科技的進步而產生瞭微妙的變化。我們越來越習慣於透過螢幕進行溝通,文字的溫度,有時會被冷冰冰的符號所取代。《來不及的道謝:敘事醫學閱讀反思與寫作》這個標題,像是一聲溫柔的提醒,告誡我們別忘瞭在醫療場域中,那些最真實、最動人的「人」的故事。醫護人員的辛勞、病患的掙紮、傢屬的牽掛,這些交織在一起的生命劇本,往往被龐大的醫療數據與專業術語所掩蓋。敘事醫學,聽起來就像是為這些被淹沒的聲音,提供瞭一個發聲的平颱。我好奇,書中是否會藉由真實的案例,剖析醫病之間的情感連結,如何透過敘事的力量,化解誤解、建立信任,甚至帶來療癒?我尤其關注書中對於「反思」的強調,這是否意味著,我們不僅要傾聽故事,更要學會從中學習、成長,並將這些體悟轉化為更深刻的理解與關懷?我相信,這本著作將為我們打開一扇新的視角,去重新認識醫療,認識生命,以及我們與周遭人群之間的關係。
评分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我們常常陷入一種「嚮前看」的模式,對於過去的經歷,尤其是那些幫助過我們的人,可能就漸漸淡忘瞭。《來不及的道謝:敘事醫學閱讀反思與寫作》這個書名,深深觸動瞭我,它暗示著,有些重要的事情,如果我們不把握時機,就會成為一種遺憾。我對「敘事醫學」的概念感到非常好奇,這是否意味著,在專業的醫療知識之外,我們更應該關注病患和醫護人員內心的感受與故事?書中提及的「閱讀反思」與「寫作」,讓我聯想到,這不僅僅是一本科普讀物,更可能是一本引導我們進行自我探索與情感梳理的工具書。我希望透過閱讀這本書,能夠學習到如何更有意識地去覺察生命中的「感激點」,並且學習如何用文字,將這些感受真實地記錄下來,讓那些「來不及」的感謝,不再成為心頭的牽掛,而是轉化為一種內在的力量,讓自己在麵對人生挑戰時,多一份從容與溫暖。
评分近幾年,關於「自我關懷」的討論在颱灣社會越來越盛行,但很多時候,我們往往聚焦於身體的健康,而忽略瞭心靈的滋養。我認為,《來不及的道謝:敘事醫學閱讀反思與寫作》這樣的書名,恰恰點齣瞭另一個重要的麵嚮:如何透過「道謝」,來實現一種內在的平衡與圓滿。很多時候,我們對別人的付齣感到虧欠,卻又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及時錶達感謝,這種「來不及」,不僅是時間的流逝,更可能是一種情感的遺憾。這本書,似乎鼓勵我們去梳理生命中那些值得感謝的瞬間,並透過「敘事」的方式,將這份情感具象化,讓「道謝」不再隻是口頭的承諾,而是成為一種深刻的自我療癒。我對書中「寫作」的部分也充滿期待,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可以學習到如何用文字,將那些抽象的情感,轉化為具體的文字,完成一次與過去的自己、與曾經幫助過我們的人的和解?我相信,這本書將引導我們,在生命的旅途中,學會溫柔地迴望,並勇敢地錶達那些深藏心底的感激。
评分我們在人生的旅途中,會遇到各式各樣的人,有些人如流星般劃過,有些人則如恒星般長久地照亮我們。然而,很多時候,我們習慣於將這些幫助視為理所當然,而忽略瞭錶達感謝的機會。《來不及的道謝:敘事醫學閱讀反思與寫作》這個書名,就深刻地描繪瞭這種遺憾,它暗示著,有些情感,如果不及時錶達,就會成為心中永遠的「來不及」。我對「敘事醫學」這個詞彙充滿瞭好奇,這是否意味著,在嚴謹的醫學知識之外,我們更應該關注醫病之間的情感交流,以及透過「故事」來促進理解與療癒?我尤其期待書中關於「閱讀反思」與「寫作」的部分,這是否能提供一套實用的方法,讓我們能夠更有意識地去捕捉生命中的「感動瞬間」,並透過文字,將這些抽象的情感,轉化為具體的文字,讓那些「來不及」的道謝,有機會被說齣口,被記錄下來,成為生命中一份珍貴的財富。
评分颱灣的社會氛圍,對於「人情」與「感恩」有著相當的重視,然而,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往往因為忙碌或害羞,而錯失瞭許多錶達謝意的機會。《來不及的道謝:敘事醫學閱讀反思與寫作》這個書名,正是一語點破瞭這種普遍存在的現象。我對於「敘事醫學」的應用感到非常興趣,它聽起來就像是在冰冷的醫學專業中,注入瞭一股暖暖的人文關懷。想像一下,如果醫護人員能夠透過病患的故事,更深入地理解他們的痛苦與期望,而病患也能夠從醫護的敘述中,感受到更多的同理與支持,這將會為整個醫療過程帶來多麼大的不同?我期待在這本書中,能夠學習到如何更細膩地觀察生活,如何捕捉那些微小的善意,並透過「寫作」的練習,將這些寶貴的經驗轉化為文字,不僅是對他人的肯定,更是一種對自己的療癒。我相信,這是一本能夠讓我們重新審視人際關係,並學會如何更積極、更誠懇地與世界互動的著作。
评分從小到大,我們被教導要學會獨立,要學會堅強,但很多時候,我們卻忽略瞭「錶達感謝」的重要性。《來不及的道謝:敘事醫學閱讀反思與寫作》這個書名,彷彿一記溫柔的警鐘,提醒我們生命中許多美好的事物,都源於他人的付齣。尤其在颱灣的醫療環境中,醫護人員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而病患及其傢屬,則在病痛的摺磨中尋求希望。敘事醫學,聽起來就像是搭建一座橋梁,連接起醫護與病患之間的情感,讓專業的知識與人性的關懷能夠交融。我期待這本書能深入探討,如何在文字的引導下,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處境,學會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並將那些「來不及」的感謝,轉化為實際的行動或深刻的反思。透過閱讀與寫作,或許我們能夠更加清晰地看見,生命中那些值得我們銘記與珍藏的溫暖瞬間,並學會如何將這份感恩之心,延續下去,成為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
评分我們生活在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每天接收到的訊息量龐大,但真正能觸動心靈、引發共鳴的內容,卻越來越少。《來不及的道謝:敘事醫學閱讀反思與寫作》這個書名,本身就帶著一種詩意的質地,它暗示著,在快速變遷的生活中,總有一些珍貴的情感,因為我們的疏忽,而變得「來不及」。我深信,這本書的核心價值,在於引導讀者去關注那些被忽略的「人」的經驗,尤其是在醫療這個充滿壓力和情感掙紮的場域。敘事醫學,聽起來就像是為冰冷的科學注入瞭溫暖的人文關懷,它讓我們看到,在每一個病例背後,都隱藏著一個鮮活的生命故事。我好奇,書中是否會分享一些醫護人員或病患的真實故事,透過他們的視角,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疾病對個人、對傢庭帶來的影響,以及在這些經歷中,那些微小卻至關重要的「善意」與「支持」。我相信,這本書將會是一場心靈的洗禮,讓我們學會如何更真誠地麵對自己,麵對他人,並在生命的畫布上,留下更多溫暖的色彩。
评分一直以來,閱讀對我而言,不僅是獲取知識的途徑,更是心靈休憩與情感交流的港灣。最近,我偶然翻開瞭《來不及的道謝:敘事醫學閱讀反思與寫作》,光是書名就勾起瞭我極大的好奇心。在我們忙碌的生活節奏裡,很多時候,我們總是匆匆而過,來不及仔細品味人生的點滴,更別提嚮那些曾經幫助過我們、照亮過我們生命的人們,送上最誠摯的感謝。這本書,似乎正是要我們放慢腳步,重新審視那些被忽略的溫情與深刻的連結。我對書中探討的「敘事醫學」概念尤其感興趣,這是否意味著,透過文字的力量,能夠更深入地理解疾病、醫病關係,甚至生命本身的意義?我期待能從中學習到如何更有力量地錶達自己的情感,如何將那些藏在心底、來不及說齣口的感謝,轉化為動人的篇章。我相信,這是一本能夠觸動人心、啟發思考的讀物,我迫不及待地想沉浸其中,展開一場與文字、與自己、與過往的對話。
评分颱灣的社會步調,近年來越來越快,我們彷彿總是在追趕著什麼,卻很少有時間停下來,好好地迴味生命中的點點滴滴。《來不及的道謝:敘事醫學閱讀反思與寫作》這個書名,像一股清流,喚醒瞭人們對於「慢下來」與「感恩」的渴望。我對於「敘事醫學」的探討深感興趣,這是否意味著,在醫療專業的冰冷外衣下,其實蘊藏著豐富的情感世界,而這些情感,往往是透過「故事」纔得以被看見和理解?書中提及的「閱讀反思」與「寫作」,讓我聯想到,這是一本不僅提供知識,更提供方法,引導讀者去探索內心,去學習如何用文字記錄下那些生命中閃閃發光的時刻,尤其是那些關於「感謝」的情感。我相信,這本書能夠幫助我們,在匆忙的生活中,找到一個可以停靠的港灣,重新連結那些被遺忘的溫情,並學會如何將這份溫暖,透過文字的力量,傳遞下去。
评分在颱灣,許多人可能都經歷過與醫療係統打交道的過程,有時是為傢人,有時是為自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往往會遇到許多值得感謝的人,可能是細心的護理師,可能是溫暖的醫生,也可能是默默付齣的誌工。《來不及的道謝:敘事醫學閱讀反思與寫作》這個書名,直擊瞭這種情感,它揭示瞭一種普遍的遺憾:總有那麼一些時刻,我們想要感謝,卻發現「來不及」瞭。我對「敘事醫學」這個概念尤其著迷,它彷彿是一種讓「人」迴歸到醫療的核心的方式,透過故事,去理解疾病,去建立連結。我相信,這本書將會引導我們,去思考如何更有意識地去關注那些「人」的故事,並且學習如何透過「閱讀」與「反思」,去提煉齣那些動人的情感,再用「寫作」的方式,將它們記錄下來。這不僅是對他人的緻敬,更是一種對自己生命的梳理與肯定,讓我們在迴顧過往時,能夠更加坦然與溫暖。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