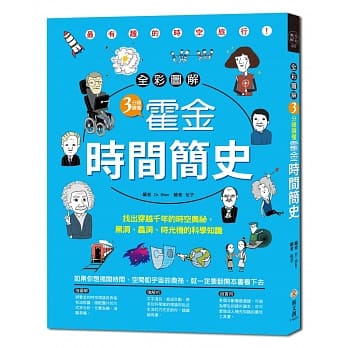具体描述
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与哲学革命,永远改变了人类的宇宙观,
也永远改变了人类对自己在宇宙所居位置的看法。
「一部十七世纪思想研究的重要作品。」────汤玛斯.孔恩(Thomas Kuhn)
◆◆◆ 中正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 陈瑞麟 专文导读 ◆◆◆
本书是科学史经典名着,作者为科学思想史学派创始人亚历山大.夸黑。书中描述,十六、十七世纪的人类心灵,遭遇了一场深度的革命;它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架构和模式,古代那个秩序井然的封闭世界(cosmos)最终变成了均一的无限宇宙(universe),价值世界也与事实世界完全分离开来。而希腊与中世纪天文学的地球中心宇宙,亦被现代天文学的无中心宇宙所取代。近代科学与近代哲学既是这场革命的根源,也是它的成果。
夸黑首次提出「科学革命」一词,以人类的宇宙观及人类于宇宙所居位置的转变来诠释这场革命,并揭露其对现代世界的深刻影响。他所揭示的新的科学史研究方法,以哲学导向来研究科学思想的发展,不仅扭转了原先萨顿百科全书式的大综论,更奠基了科学史研究的地位及重要性;夸黑及其科学思想史学派所描绘的「科学革命」,已然成为当今社会大众理解的科学发展轮廓。
目录
哲学人系列总序
导读 「无限宇宙」的思想探险 陈瑞麟
译序与致谢
野口英世医学史讲座
序
导论
第一章 天穹与天界
库萨的尼可拉与帕利坚尼斯
第二章 新的天文学与新的形上学
哥白尼、狄吉斯、布鲁诺与吉伯特
第三章 新天文学反对新形上学
克普勒对无限的驳斥
第四章 前所未见的事物与前所未思的思想:发现世界空间中的新星与空间的物质化
伽利略与笛卡儿
第五章 不受限定的展延还是无限的空间
笛卡儿与摩尔
第六章 上帝与空间、精神与物质
摩尔
第七章 绝对空间、绝对时间与它们和上帝的关系
马勒布朗雪、牛顿与宾利
第八章 空间的神圣化
拉弗森
第九章 上帝与世界:空间、物质、乙太与精神
牛顿
第十章 绝对空间与绝对时间:上帝的行为框架
柏克莱与牛顿
第十一章 工作日的上帝与安息日的上帝
牛顿与莱布尼兹
第十二章 结论:工匠神与无所事事的上帝
著者信息
亚历山大.夸黑
Alexandre Koyré(1892-1964),科学与哲学史学家,法国着名科学思想史大师,曾师从胡塞尔,在科学史上地位不亚于萨顿(George Sarton)。吉利斯皮(Charles C. Gillispie)、霍尔(A. Hall)、威斯特福尔(R. Westfall)、科恩(I. B. Cohen)等人均曾将夸黑视为他们的思想导师。
他以哲学的导向来研究科学思想的发展,认为人类的求知活动(宗教、哲学与科学)必须被视为一个历史的有机体。夸黑在法国、美国与义大利等地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着作包括:《论伯麦的哲学》(La Philosophie de J. Boehme, 1929)、《伽利略研究》(Etudes Gaileennes, 1939)、《天文学革命》(La Revolution Astronomique, 1961)。
译者简介
陈瑞麟
中正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曾任台湾科技与社会研究学会理事长。长期耕耘于科学哲学、科技与社会、自然哲学与科学史等领域。着有《科学理论版本的结构与发展》(台大出版中心,2004)、《科学哲学:理论与历史》(群学,2010)、《认知与评价:科学理论与实验的动力学》(台大出版中心,2012)、《科学哲学:假设的推理》(五南,2014)等。
张乐霖
崇右企专企管科毕业,东吴大学哲学系毕业,东吴大学哲学研究所肄业。
图书目录
哲学人系列总序
导读 「无限宇宙」的思想探险 陈瑞麟
译序与致谢
野口英世医学史讲座
序
导论
第一章 天穹与天界
库萨的尼可拉与帕利坚尼斯
第二章 新的天文学与新的形上学
哥白尼、狄吉斯、布鲁诺与吉伯特
第三章 新天文学反对新形上学
克普勒对无限的驳斥
第四章 前所未见的事物与前所未思的思想:发现世界空间中的新星与空间的物质化
伽利略与笛卡儿
第五章 不受限定的展延还是无限的空间
笛卡儿与摩尔
第六章 上帝与空间、精神与物质
摩尔
第七章 绝对空间、绝对时间与它们和上帝的关系
马勒布朗雪、牛顿与宾利
第八章 空间的神圣化
拉弗森
第九章 上帝与世界:空间、物质、乙太与精神
牛顿
第十章 绝对空间与绝对时间:上帝的行为框架
柏克莱与牛顿
第十一章 工作日的上帝与安息日的上帝
牛顿与莱布尼兹
第十二章 结论:工匠神与无所事事的上帝
图书序言
现代科学的宇宙观,对人类历史有无可比拟的深远影响。尽管我们都生活在它的笼罩之下,对它的诞生与崛起的历史,却近乎一无所知。通俗的科学观告诉我们,十六世纪的天文学家哥白尼(Copernicus)提出了「地动说」之后,现代科学英雄如布鲁诺(Bruno)和伽利略(Galileo)等人,无惧于教会的打压,以无比的毅力推动科学革命,终于在牛顿(Newton)的手中完成。自此之后,人类的宇宙观摆脱了基督教会神学家的哲学玄想,步入了实证的科学时代。这幅历史图像,把基督神学与科学思想对立起来,把哲学(形上学)玄想与科学研究对立起来。然而,它恰当吗?
夸黑(Alexandre Koyré)这部科学史的经典名着《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告诉我们,历史的实际发展,远比通俗科学观要复杂许多。在夸黑的笔下,现代科学革命的核心,乃是打破亚里斯多德的封闭世界观(为基督教神学继承),建立现代科学的无限宇宙观。其间的发展曲曲折折。卷入这场大论辩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们,并不能被简单地二分成「教会神学/玄学家」对立于「近代实证科学家」。相反地,对立的两方或差异的多方都信仰上帝──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和观念来理解祂;他们都从事哲学/形上学的玄想──那是他们的科学方法与内容之一;他们也都努力思索无法实证的空间、时间与运动的本质──这些概念是科学理论的必要成分;他们甚至也都是神学家──因为他们都试图去理解「上帝」、上帝的特征以及上帝和空间与宇宙的关系。
科学确实在十七世纪时完成了一场革命,可是,这场革命无法与哲学的转变分隔看待,诚如夸黑所言:「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同时是革命的根源与成果」。《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就是在展示这场科学与哲学宇宙观革命的丰富历史,与它的深度、广度和演变的曲折性。
近代科学的宇宙观革命
在《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的舞台上,开启宇宙观大革命序幕的是库萨的尼可拉(Nicholas of Cusa)——一位想像力大胆超卓的教会哲学家。教会官方认可的封闭世界观在他手中绽开第一道裂缝。后继的思想家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和区域下手,联合使这「世界泡泡」(world-bubble)爆涨成无限宇宙。
希腊大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在西元前四百年左右,即建立了一套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他把整个世界分成「地界」(terrestrial region)(或「月下区域」〔sublunar region〕)和「天界」(celestial region)(或「超月区域」〔superlunar region〕),两个界域有截然不同的质料和形式。「月下区域」包括地球,以及从地球到月球之间的空间。地球由「土元素」构成,表面覆盖着「水」,水之上方是「气」,气的外层为「火」(流星、彗星等现象即「火元素」的作用)。从月球所在的场所往上,即是「天界」,其结构是一层又一层的同心球壳,依序是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土星和第八层的「恆星天球」(stars sphere)。构成天界的物质乃是和土水气火四元素截然不同的第五元素——乙太(ether)——它是一种透明固体结晶状的物质。这样的宇宙结构,很像一颗正圆球状的洋葱,恆星天球则是世界的极限。至于恆星天球之外是什么?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对亚里斯多德来说,那超出了我们经验的界限。
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哲学家,完全接受亚里斯多德的宇宙结构理论,因为它可以很融洽地配合基督教的神学观。上帝被设想为「居住」在恆星天球上方,那也是天国所在。当然它不属于物质王国,而是纯精神性的。精神不必占有空间,所以恆星天球之外,也不存在空间;世界和空间整个地被封闭在恆星天球之内。而且天界、地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月下区域变动不定,是世俗的、卑下的;天体区域则是不变的、永恆的、完美的,诸天球壳层进行均匀规律的圆周运动。可是,天体的运动又是怎么产生的?亚氏认为那是世界因果变化的第一因,即「第一动者」(primary mover),又称作「不动的动者」(unmoved mover)。在教会思想家看来,这就等于是「上帝」。因此,这样的世界除了封闭之外,也拥有一个层级分明的结构。
无限宇宙的早期孕育者库萨的尼可拉利用他所谓「博学的无知」(learned ignorance),主张一切事物都存在着「对立统一」。其证明方法乃是把有限对象加以「无限化」之后,就会显示出「对立统一」。例如,「直线」与「曲线」是对立的,可是在无限大的圆之中,曲线的圆周就等于直线的切线;在无限小的圆之中,曲线的圆周等于直线的直径。把这套推论方式应用到世界本身,就会推出世界不可以有中心和周界,如果它有中心,就意味有周界,有周界就有周界之外的事物和空间,如此所谓的世界就不是真正的世界。因此,世界不可能是有限的。但尼可拉也没有立刻主张世界是无限的,因为「无限性」只能被归属于上帝。尽管如此,他的思想仍然炸开了封闭世界的第一条裂缝。
哥白尼虽然被后世尊为天文学革命的发动者,其实他的世界观却是相对地封闭而保守。他仍然持有一个亚氏的洋葱状世界,只是把宇宙的中心换成太阳。可是,既然他让地球运动,就颠覆了旧世界观固有的层级结构。同时,他的颠覆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后果——我们不再需要恆星天球,因为恆星天球的存在目的是为了说明恆星的共同运动(东方昇起西方落下),既然地球自转可以说明这个现象,那我们又何需第八天球?因此,布鲁诺就首度大胆明确地引申出「无限宇宙」的概念。对布鲁诺来说,一个有限世界的界限之外,仍然是空间。既然上帝创造了世界,祂怎么可能对界限之内和之外有差别待遇呢?因此上帝所创造的,必然是个无限空间的宇宙,同时也没有道理想像上帝对于地球所处的太阳系特别偏爱,上帝必然创造了无数类似于我们太阳系的星系世界,也有无数的居民(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外星智慧生物」)生存在无数世界之中。可是,布鲁诺的「无限宇宙和无数世界」观过于离经叛道,不仅受到教会的宗教打压,也受到大天文学家克卜勒(Kepler)的科学性驳斥。
克卜勒卓越地论证,无限空间的观念与我们的星空经验并不符合。虽然克卜勒定律在天文学革命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的太阳崇拜思想也使他坚持哥白尼的太阳中心理论。可是,夸黑告诉我们,克卜勒坚持我们太阳系的独特性,而且在形上学的存有和运动概念方面,克卜勒仍然有着亚氏的老观念。紧接着,伽利略透过望远镜,看到许多前所未见的星体;尽管如此,伽利略似乎不愿参与「宇宙是有限或无限」这议题的论辩,他感到无解,或许只有神启才能告诉我们。可是,伽利略主张封闭的圆周运动是「自然运动」(即今日的惯性运动),所以,他的世界很有可能还是封闭的,或许顶多只是尼可拉式的「不受限定的」(indefinite)。
到目前为止,尽管思想家们已不再接受教会的「地球中心观」,但对于宇宙的尺度究竟有无限界则未有共识。然而,上帝作为第一推动者、而且持续不断地「推动」宇宙的观念,并没有人怀疑。只有笛卡儿(Descartes)企图以数学几何的规则来作为万物因果变化的直接依据。当然,笛卡儿并没有拒绝上帝存在,也没有否定上帝创造世界,可是,他认为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初,同时也创造了数学几何的规则来「管理」(维系)世界,此后世界就如同一台被启动的机器般,持续不断地根据规则而规律地运转,再也毋需上帝介入。如此一来,笛卡儿也必须回答:星体究竟是怎么运动的?他提出了涡漩理论(vortex theory),主张每个星系是一个巨大的天寰涡漩(heaven vortex),恆星(太阳)居于涡漩核心,行星是被涡漩所带动而环绕恆星运转。这样看来,笛卡儿赞同布鲁诺,主张在我们的世界太阳系之外,还有许多恆星系。可是世界是无限的吗?笛卡儿像尼可拉一样,认为「无限性」只能是上帝的属性。所以,世界顶多是「不受限定的」,又因为笛卡儿相信「展延与物质是同一的」,世界和世界的空间都是「不受限定的展延」(indefinite extension)。
在剑桥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摩尔(More)看来,笛卡儿的理论等于把上帝驱逐出世界之外,无异于无神论。而且所谓「不受限定的展延」这个观念令人费解,在摩尔看来,世界若不是无限的,就是有限的,没有第三种可能。因为上帝的无限性与无所不在,使得世界必是无限的,若不然上帝就不可能既无限又无所不在。这样看来,展延也不能与物质同一,因为精神性的存有者也有其展延。另一方面,「空间与物质同一」的说法,不仅忽略了空间(真空)的实在性,也掩盖了它的神性。空间是真空,不是虚空。再者,传统神学家归属给上帝的属性如单一、单纯、永恆、不可动、在己存有、独力存有、不可毁坏、无形、必然等等,都同样可归给空间。空间其实正是上帝的属性,世界所在的无限空间正是上帝自己的展延。
摩尔这种观念,绝不是「失落在新科学世界中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的神祕幻想。正好相反。在最基本的特征上,它是那时代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所共享的主张」,这些思想家包括牛顿。牛顿,有时被视为古往今来科学第一人,他建立了现代科学的理论体系、方法和形式。可是,牛顿所谓的自然哲学「数学研究」或「实验研究」中,也不能缺少形上学的思辨。他区分了「绝对空间」(absolute space)与「相对空间」(relative space),前者是绝对的、真实的、不可动的空间,后者则是相对的、可动的、可测量的、依赖于物质的笛卡儿式空间。牛顿甚至进一步说:「无限空间好像是上帝的感觉中枢。」正是这句话引发莱布尼兹(Leibniz)的强烈批判。
牛顿的上帝不仅拥有空间的属性(展延到无限宇宙的每个地方),还有主动、积极的力量:上帝的精神作用正是万有引力的原因,同时也是宇宙间一切现象(如物质的凝聚、化学作用、光、生物的生理等等)的直接原因。因为在牛顿看来,笛卡儿诉诸「纯机械作用」,顶多只能说明一些碰撞运动,那是物体运动的被动原则,如果想以这种纯机械作用来说明上述现象,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妄想假设了。牛顿坚持他的实验哲学容不下这种妄想假设。要说明万事万象,非得要有一「主动原则」(active principle)不可——就是上帝(的精神力)。
可是,对莱布尼兹而言,牛顿的观念让上帝成为一位低能的钟表修理匠,祂所创造的世界是这么地不完美,以致祂必须时时介入,不断地为世界钟上紧发条。同时,牛顿所谓「空间是上帝的感官」,贬抑了上帝的地位和能力,使祂必须依赖于某个器官。莱布尼兹坚持笛卡儿的二元论——精神不可能占有空间,也不具展延性,如果上帝是纯精神,当然祂是无所不在的,但这并不是物质性的展延,宣称上帝有展延性,就是把上帝贬抑为物质。至于运动的观念这方面,他也延续笛卡儿、柏克莱(Berkeley)的传统,批判牛顿的绝对空间与绝对运动(absolute motion)的概念。莱布尼兹的严厉批判不能没有回应和反驳,可是牛顿厌恶自己下场,他的忠实弟子与友人克拉克博士(Clarke),就成为牛顿理论的代言人,在这场纵贯两百多年、关于「空间、运动和上帝」的大论辩中,和莱布尼兹共同扮演结辩的角色。夸黑则以「工作日的上帝」和「安息日的上帝」鲜活地比喻牛顿和莱布尼兹的上帝观之差异。
当然,这场论辩并没有共识,也没有结论,甚至没有明确的胜方败方。「封闭世界」的旧观念,自然是退隐了(不过,它在二十世纪初卷土重来),「无限宇宙」的新学说闪耀于科学与哲学的舞台上。可是,这并不意味牛顿的整个理论相对于笛卡儿思想的全面胜利,至少在上帝观念和角色方面,牛顿的上帝在牛顿力学日后的发展中,也悄然地隐没;十八世纪后半的科学家转而支持莱布尼兹式的世界钟,相信它会根据能量守恆原理,永恆无止境地运转下去——当然,在一个无边无际的无限空间中。
本书的意义
《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乃是夸黑的系列演说,于一九五三年首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野口英世医学史讲座」(Hideyo Noguchi lecture)发表,后来在一九五七年把讲稿增订出版。在本书的演说成书期间,西方世界的科学观笼罩在实证论的支配之下,拒绝形上学玄思在科学进展中的影响。诚如孔恩(Thomas Kuhn)所言:「科学史家惯于忽略玄思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而他的哲学同事则对科学的非方法论成分有所戒心。」本书一反常态,不仅联结哲学与科学,而且卓越地展示了在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时期,哲学和科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过去,在哲学史的阅读中,哲学学生总是对十六到十八世纪的形上学感到深奥难解。我们不知道摩尔、史宾诺莎(Spinoza)、马勒布朗雪(Malebranche)、莱布尼兹这些大哲学家,为什么要提出那些玄之又玄的形上思想?他们提出的东西似乎是纯然幻想,与我们的经验拉不上关系。在读了《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之后,原本看似毫无根基的形上学玄想,现在都可以和科学(天文学)研究键结起来,而且变成科学思考的必要成分。换言之,如果我们想真正掌握十七和十八世纪现代欧洲哲学史,我们不能略过本书。
反过来看,《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当然是一本「科学史」的经典。可是,这部科学史和传统科学史家笔下的科学史截然不同,它没有从十八世纪后的牛顿标准来看待先前的科学,相反地,它证明了十六、十七世纪的形上学玄想,对当时科学议题的提出、科学研究的方向、理论概念的塑造,有十分深远的启迪作用;甚至将它们视为科学思想的必要成分也不为过。再度如孔恩所言,夸黑的着作「证明了忽略科学与哲学之间的边界地带是多么地不幸。不管玄思与否,对于物理无限的创意关怀,必定是十七世纪思想的普遍创意元素之一。」
夸黑与《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的影响
夸黑(1892-1964)生于俄罗斯,一九二九年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法国教学研究。早期以哲学思想史研究为主,一九三二年起开始研究科学史。一九三九年出版《伽利略研究》(Études galiléennes),从此奠定他在科学史研究中的地位。 一九五五年他应聘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Princeton),直到一九六四年去世为止。他的论着以法文为主,但在生命最后十年之间,他往来于巴黎和普林斯顿讲学研究,期间也出版不少英文论着,如《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牛顿研究》(Newtonian Studies)、《形上学和测量》(Metaphysics and Measurement)等书。由于夸黑的出身、讲学和研究横跨俄罗斯、法国和美国,也因为他的哲学、思想史背景,还有他採取的方法和史观,使得他的影响力跨越地域、文化和学科的界限。
夸黑的深远影响,可就几个不同层面来看待。首先,夸黑的研究方法是所谓的「文本解释」(explication des texts),也就是引用大量第一手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文献,从事分析和解释。文本解释在文学、哲学、历史甚至社会学等人文社会学科方面并不新鲜,可是西方文化传统总是认为(自然)科学相当不同于人文,不能或不该以研究人文文献的方法来研究科学历史。夸黑的工作正是对此一观点的有力反驳或矫正。除了第一手文献的解释外,夸黑的文本分析还考虑到科学思想的整体性,以及文本背后的整个思想脉络或时代气候:每位大科学思想家的思想和文本,都有其内在外在的融贯性,科学史家应该根据科学思想家的关注问题和独特观点来理解他的理论,解释他的着作,而不是如实证论般把他们的科学思想体系拆成片片段段,再根据后世的科学标准来剪裁取舍。
其次,夸黑的科学史研究的一个重心是,他聚焦在十六到十七世纪这一段近代科学革命时期,致力于揭示科学思想的发展与哲学概念转变两者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提供的图像尤为鲜明,这一点我们已在〈本书的意义〉中揭示。然而,更重要的是,它也影响和预示了孔恩的「典范」(paradigm)观念:「形上信念」是每个科学典范的必要元素。
第三,《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宏观而完整地描绘了十七世纪科学革命背后的「宇宙观革命」:从亚里斯多德─托勒密(Ptolemy)-基督教会的「封闭世界」转换到布鲁诺-摩尔和牛顿的「无限宇宙」,两者之间巨大差异,可用「断裂」来形容。这样一幅革命图像也影响或预示了孔恩的典范之间「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的观念。
最后,我们应该专门谈谈夸黑和本书对孔恩的影响。孔恩在一九五七年出版他的科学史论着《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一九五八年为《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写了一篇书评,其中已预示了他在一九六二年《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的「典范」和「不可共量性」,孔恩在书评中如是地解读夸黑提出的图像:
「在亚里斯多德主义者和早期哥白尼式的宇宙,上帝的宝座在最外层的天球之外。在笛卡儿和牛顿的无限宇宙中,则不再有如此的位置;因此,只有内在的神(immanent Deity)才能持续地推动祂的创造物。结果是,十七世纪思想的一个持续潮流是把上帝指认为空间或充满流体的空间。在这个世纪之间,先前新柏拉图主义的世界魂(anima mundi)那种神祕而不可沟通的景象,逐渐地变成理性自然神学的必然性。」
除此之外,夸黑的科学史方法论也影响了孔恩,正是在「考察科学家和学派自身思想脉络的融贯性与发展的继承性」这样的观点之下,孔恩才能提出他的典范理论。只是夸黑重视思想发展本身的内在脉络,而孔恩还进一步强调外在的社会背景和环境──当然,这个强调也打开了科学史研究的新局面。
总而言之,《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是我们了解十七世纪科学革命史的经典着作,同时也是了解十七世纪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必要文献。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这本《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近代科学与哲学的宇宙观革命》带给我的震撼,不仅仅是对宇宙本身认知的拓展,更是对科学精神和哲学思辨的深刻理解。作者在描述伽利略如何用望远镜观察星空,颠覆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时,那种充满细节的文字,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感受着每一次观测带来的惊喜和质疑。我尤其喜欢书中对“无限宇宙”概念的探讨,从早期哲学家们对无限的恐惧和排斥,到后来 Giordano Bruno 提出宇宙无限的猜想,再到现代天文学家们对宇宙膨胀和无边无际的探索,这个过程充满了人类智慧的闪光点。这本书让我明白,科学的进步并非线性向前,而是充满了反复、争议甚至牺牲。比如,布鲁诺因为他的宇宙无限论而被处以火刑,这其中的悲壮,让我对科学的殉道者们肃然起敬。同时,作者也将哲学中的“存在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思潮与科学革命的进程紧密结合,展现了科学与哲学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启发的辩证关系。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不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宇宙观察者,而是开始思考,我们作为宇宙的一部分,我们的存在又意味着什么?这本书的启发性,真的远超我的想象。
评分这是一本让我重新审视“宇宙”这两个字的厚重感、历史感和思想深度的好书。《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近代科学与哲学的宇宙观革命》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科学史的书,更是一场关于人类如何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的哲学之旅。作者在讲述从亚里士多德的“天上地下”分层宇宙,到近代天文学家们逐渐打破这种界限的过程中,那种层层递进的逻辑和清晰的阐述,让我大呼过瘾。我特别欣赏书中对“可见光”和“不可见光”在天文学观测中的作用的描述,让我意识到,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仅仅是宇宙的一小部分,而科学的进步,就是不断拓展我们感官的边界。书中对“星系”概念的形成,以及我们从银河系之外还有无数“星云”的认识,到后来发现它们都是独立的“星系”,这个认知的演变过程,充满了曲折和惊喜。作者还将当时欧洲的思想文化背景,比如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与科学革命的进程穿插讲解,让我理解了科学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和文化土壤之中。这本书让我明白,我们今天的宇宙观,是无数先辈智慧和努力的结晶,而探索宇宙的脚步,也必将永不停歇。
评分《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近代科学与哲学的宇宙观革命》这本书,让我感觉像是在参加一场跨越几个世纪的思想盛宴。作者的笔触非常细腻,他不仅描述了科学家的发现,更深入地挖掘了这些发现背后的思想动机和哲学困境。我尤其喜欢书中关于“宇宙膨胀”和“大爆炸”理论的讲解,作者用非常浅显易懂的语言,解释了哈勃定律和宇宙学红移现象,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到,我们所处的宇宙并非静止不动,而是在不断地膨胀,并且可能有一个起始点。这种宏大的视角,让我感到自身的渺小,却又充满了对宇宙奥秘的敬畏。书中对“黑暗物质”和“黑暗能量”等现代宇宙学前沿的介绍,也让我看到了科学探索的永无止境。而且,作者并没有回避科学理论中存在的争议和未解之谜,这反而让我觉得这本书更加真实和可信。他巧妙地将康德的“先验理性”、休谟的“经验主义”等哲学思想与科学发展相结合,展现了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科学与哲学是如何互相启发、螺旋上升的。这本书不仅增长了我的科学知识,更激发了我对存在、对宇宙终极命运的深层思考。
评分读完《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近代科学与哲学的宇宙观革命》这本书,我真的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好像过去几十年对宇宙的理解都是雾里看花,直到翻开这本厚实的著作,才如拨云见日。作者的叙事非常流畅,从古希腊哲学家们简陋但充满智慧的宇宙模型开始,一步步勾勒出人类对宇宙认知的演进。尤其是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的那个部分,读来惊心动魄,仿佛亲身经历了当时科学界和宗教界的巨大冲突,也深深体会到,每一次重大的科学飞跃,背后都伴随着巨大的勇气和颠覆性的思想。书中对于牛顿力学如何将宇宙“尺度化”和“机械化”的描述也相当精彩,让我明白了我们如何从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由神明主宰的宇宙,逐渐走向一个可以用精确数学和物理定律来解释的、巨大的、有规律的机器。这种从“何处来”到“如何运转”的转变,真的是人类理性力量的伟大体现。而且,作者并没有停留在纯粹的科学描述,而是巧妙地将哲学思考融入其中,探讨了这些科学革命对人类自身定位、对自由意志、对存在意义的深远影响。我常常在想,如果当时没有这些先行者,我们如今对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又会是什么样的认知呢?这本书让我觉得,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许多观念,背后都有着如此曲折而深刻的历史。
评分坦白说,一开始我被《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近代科学与哲学的宇宙观革命》这个书名吸引,但抱着的是一种“看看近现代科学怎么解释宇宙”的心态。然而,这本书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它并没有一股脑地堆砌科学名词和公式,而是用一种非常生动、引人入胜的方式,讲述了人类宇宙观的“大地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恒星”概念的转变,从古代认为它们是镶嵌在天球上的固定发光体,到后来意识到它们是遥远的太阳,拥有自己的行星系统,这个认知的飞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书中对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的阐释也相当到位,我一直以为那些公式是枯燥难懂的,但作者通过历史故事和形象的比喻,让我理解了这些定律背后蕴含的优雅和普遍性。更让我惊喜的是,作者对“时空”概念的演变也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从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个跨越,不仅仅是物理学的革命,更是哲学上对现实本质的重新定义。这本书让我觉得,原来我们头脑中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常识”,在科学家的眼中,是多么的“不靠谱”。这种颠覆性的思考,让我对世界的理解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