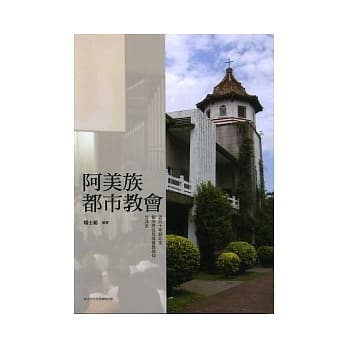具体描述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为晚期拉丁文学的代表作,也是古代西方文学名着之一。此书更启迪了廿世纪「诸现象学运动」,包括胡赛尔、海德格、吕格尔、德希达、马希翁、卡布托等人都分享到了此书的睿见。再读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将带领读者更细腻地阅读书中的文字,更深刻感受奥古斯丁对自身过去记忆的回忆与诠释。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西方十大经典之一,其宗教、文体、思想、写作风格以及深刻的人生经历对神学、哲学或其他学门影响深远。《忏悔录》的主轴之是忏悔,仔细阅读还可发现另一主轴——祈祷。他的祷词大量地引述圣经〈诗篇〉,将〈诗篇〉咏颂般的赞美结合祈祷的语言,使《忏悔录》在文学造诣上成为经典之作。事实上,奥古斯丁的忏悔和祷告,忏悔奠基于记忆,如要忏悔必须先唤起内心深处曾经存在却被短暂遗忘的记忆,加以反省并有所体悟。事实上,除了《忏悔录》中忏悔和祈祷的语式,爱、友谊、宽恕、哭泣、死亡、母亲、视觉、慾望、哀伤、离别、痛苦都是众人所必须研读、深思的内涵。《重读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这本论文集能够引导读者对《忏悔录》有更深入及更全面的了解,并能试图从神学、文学各角度提出与自身更密切相关的见解与反思。
作者简介
曾庆豹
出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和哲学研究所,之后于国立台湾大学获哲学博士。先后任香港建道神学院客座研究员、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香港汉语基督教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神学系海外教授团成员等。目前为中原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国际期刊Sino Christian Studies主编,并主持编辑丛书系列包括「汉语基督教经其文库集成」(橄榄华宣)、「中原大学.大师系列」(基道书楼)、Sino Christian Studies Supplement Series (Tonsan Pub.)、「中国基督教公共神学文选系列」(研道社)等。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附录:「奥古斯丁的一生」绘画)
奥古斯丁的自画像—作为文学自传的《忏悔录》∕耿幼壮
后现代神学语境下对奥古斯丁《忏悔录》之再阐释∕芮欣
泪水之书—试论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哭泣问题∕陈芸
未完的哀悼:利奥塔思想探析—以《奥古斯丁的忏悔》为例∕芮欣
友谊亦或洗礼?—试析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无名朋友之死」∕花威
友谊的焦虑—对奥古斯丁《忏悔录》的一种解读∕尹景旺
内布利提乌斯的双面孔?一个有趣的对读:《忏悔录》和《书信》∕王涛
图书序言
序
奥古斯丁的祈祷与眼泪—重读《忏悔录》∕曾庆豹
我爱你已经太晚了,你是万古常新的美善,我爱你已经太晚了!你在我身内,我驰骋于身外。我在身外找寻你;丑陋不堪的我,奔向着你所创造的炫目的事物。你和我在一起,我却不和你相偕。这些事物如不在你里面便不能存在,但它们抓住我使我远离你。你唿我唤我,你的声音振醒我的聋聩,你发光驱除我的幽暗,你散发着芬芳,我闻到了,我吸取你的气息,我尝到你的滋味,我感到饥渴,你抚摸我,我在你炽热中想望着你的平安。(Confessions, X:27)
要永远记得,要赞美上帝。他要我来帮助你们,并不是我自己要来的。……当你们认为亲眼看见我吃东西的时候,实际上我什么也没有吃,你们所看到不过是拟像。(次经《多比传》十二17–19)
希区考克(Alfred Hitchcock)1953年的作品《忏情恨》(I Confess, [让我们模仿纪杰克(Slavoj zizek),从电影开始吧!纪杰克编辑出版了一本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Lacan (but were afraid to ask Hitchcock),俨然成了希区考克电影的专家。]),在法庭上为了挽救神父,证明兇杀案发生时他不在场,有夫之妇不得不公开自己与神父过去一段难以启齿的交往过程,承认自己与神父的暧昧关系。以为不坦白就无法获得宽恕,但又却使自己和神父身陷囹圄,使原来的复杂案情更添复杂。到底该不该坦白?坦白之后的心灵是否因此平静或更起伏不定?什么是忏悔的经济?
一、
《忏悔录》(Confessionum)为我们开启了近代的「笛卡儿主义」,又启迪了廿世纪「诸现象学运动」,包括胡赛尔、海德格、阿伦特、吕格尔、德希达、马西翁、卡布托等人都分享到了此书的睿见。在西方思想史上,希波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不仅仅被理解为基督教神学家,他的思想地位与柏拉图、康德并列,奥古斯丁以后,没有一位思想家敢忽略他的影响。提到奥古斯丁的着作,学界无例外地会认为《三位一体》(De Trinitate)、《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和《忏悔录》并列为他所有的着作中最为重要的三部,堪称作「神学三部曲」。而且,又以《忏悔录》被说成是最为广泛被人阅读和讨论得最多的一本,这说明了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是理解为奥古斯丁的「自传」[关于奥古斯丁的「生平」,我们可以从《忏悔录》来认识他的「前传」(46岁),我们也可以通过绘画来认识奥古斯丁,最完整且经典的代表作,无疑的,即是画在意大利托斯卡尼区的圣吉米纳诺(San Gimignano)的The Church of Sant’Agostino内的东边圣堂的十七幅(分成三个部份)奥古斯丁一生重大的事蹟,作者是Benozzo Gozzoli,此作品完成于1464–65之间]。也不是一般意义的所谓「思想着作」,更不仅仅是作为贯穿着对于他其他着作的导引性理解。
《忏悔录》写于397至401年间,全书共分作十三卷[(卷一)罪∕告白∕童年;(卷二)成长∕偷梨;(卷三)旅行的开始;(卷四)论友谊;(卷五)从迦太基到罗马;(卷六)重新理解基督教;(卷七)新柏拉图主义∕真理∕信仰与理性;(卷八)皈依∕拿起来读;(卷九)新生∕母亲莫妮卡之死;(卷十)论感官∕论记忆;(卷十一)论时间;(卷十二)论圣经诠释;(卷十三)论创世。],后面三卷明显偏离了原来「忏悔」的意识,变成是对创世记第一章的解释,因为在撰写《忏悔录》之同时,奥古斯丁正在写《创世记疏解》,对于他的「神学思想」感兴趣的人会重视后三卷的内容。可能,卷九即是《忏悔录》的最后一卷,我们应该停在这里,但是卷十却又是全本《忏悔录》最有意思的一卷,要想综合性地把握并作为入手理解《忏悔录》的思想准备工作,应该从卷十开始,卷十就像是《忏悔录》的「前言」。
《忏悔录》不属于「历史哲学的书写」(《上帝之城》),也不是「解经书」(《诗篇释义》),也不是「教义学」或神学之辩(《论三位一体》、《驳伯拉纠派》)。《忏悔录》(397–401)是一部「祈祷文」[卷十至十三除外],也是一部「赞美诗」[全书对圣经诗篇的引述极为频繁,奥古斯丁着有《诗篇释义》,其篇幅是《上帝之城》之一倍厚]。
一个人的「忏悔」是向上帝「忏悔」,我为何要去读他人的「忏悔」?一位主教为何要「公开」他的过去?纯粹为了写一部「回忆录」或「自传」(autobiography),或是想留下什么,希望人们对他的过去有更多的认识?一部「个人的忏悔录」何需认真对待,难道只因为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奥古斯丁主教,一位被视为「正统」的教父吗?[卢梭的《忏悔录》是「启蒙主义者的渎神」、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是「文学式的矫情」]
按拉丁文Confessor的意思,意指「见证」(witness),而且是自希腊文那里翻译过来带有殉道(martyr)的那种公开意义的「见证」,所以有人把《忏悔录》翻译成《证言》(The Testimony)。忏悔在祈祷的语式中是一种「坦白」,或者是「公开」自己的罪行。首先即是「坦白地说出」这个动作,而种种「说出」的都是过去的;其次,说出自己的罪行就已经是某种责罚,也是抵罪(expiation)的开始,这种坦白地说出正是对自己进行拷问的方式,即要求记忆起自己的罪行;最后,对于自己的过去必须有所了解与接受,不管是痛苦的或快乐的,形成一种经济学:「不愿坦白的痛苦」和「坦白形成对灵魂的宽慰」,悔罪即意味着寻求宽恕。[Confession(忏悔)和penitence(赎罪)在法文中是近义词,两者意思又有交叉,都有因为犯下了罪过而表示悔恨,请求上帝宽恕的意思。但是Confession更强调认罪和坦白,通过坦白来获得宽恕;而penitence则可能包括一些行动,如苦行、自我责罚等。见傅柯《不正常的人》中译者註,185]
《忏悔录》第二卷一开始说:「我愿回忆我的过去的污蔑和灵魂的纵情肉欲,并非因为我流连以往,而是为了爱你,我的上帝。」(II:1,以下引文採用徐玉芹译本,台北:志文出版社,2000)一个人的回忆何以是「为了爱」,「爱上帝」与「公开过去的污蔑和灵魂的纵情肉欲」有何关系、一种怎样的忏悔意识使我们以公开自己过去的「不是」来表达对上帝的爱?忏悔与爱、公开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上帝早已知道这一切(X:2),人又何须向祂坦白呢?坦白可能与知道(知识)无关,或许它更多的是唤起一种责任(responsibility):坦诚面对并回应(response)自己之所做所为。
祈祷不是以「什么是……?」作为开始的,奥古斯丁虽然也问到:「我的上帝究竟是什么?」(X:6),但不同于哲学的「什么是……?」,他以「爱」作为开始,一种「不得不」的爱。不同于哲学本源地提问,问:「……是什么?」,当开始了哲学,却在「问」中脱离了经验;换言之,祈祷之前,先预设了一种「关系」的存在,这样的「关系」使得祈祷得以可能,因而祈祷一开始就不是主体性的,爱从来就不是一个没有对象或不预设了存在着一位他者的爱。奥古斯丁把忏悔理解为「为了爱你(上帝)」(II:1)即为了「回应」,回应于一个早已洞悉人心底蕴的上帝,如果「爱」是作为回应的方式,就与责任联系起来。
忏悔是对欲望的扬弃吗?那么,没有欲望的爱又会是什么?[阿伦特在Love and St. Augustine中讨论了奥古斯丁将爱置于斯多亚—伯拉图式的欲望(craving)和基督教的回忆中做两难性的处理]奥古斯丁表达了他对上帝的爱基于一种「匮乏」,这正是欲望的诱饵,「除非安息在你怀中,不然我的内心无法获得安宁」(I:1)。忏悔表面上看来是一种限制欲望的表现,但是它所限制的是主体自己的欲望,而非源于他者的欲望,这种匮乏是从一个能指到另一能指的转移,通过「他者」赋予了匮乏以意义,这种欲望不是寻获满足,而是对于「不满足」的「满足」。奥古斯丁把这种欲望理解为一种来自于上帝的暗示,暗示着人的有限,因此是神圣的足迹。爱即是欲望的不可能的化身,爱即是爱那不可能者(The Impossible)。
我们和奥古斯丁一样困惑:「当我说爱上帝的时候,我爱的是什么呢?」(X:6, quid ergo amo, cum deum meum amo) 「爱上帝」究竟是「爱的是什么」,只能意味着我所爱的上帝不是一种以「某种」的方式到来的上帝,作为他者,上帝永不是为我们所爱,相反的,我们是为祂所爱[源于上帝的圣爱(caritas)],是上帝爱我们,上帝以爱的方式临在[阿伦特把这种爱解释为「邻人之爱」,所以奥古斯丁在上帝、自我与邻人之间构成「爱的秩序」,即一种友爱。奥古斯丁在《忏悔录》处处流露出「友爱」(friendship),我们要记着的是「别人的好」]。
二、
也许,我们必须改变传统那种「神学」或「教义学」式的解读。过去神学家由于职业的需要,或故弄玄虚地搬弄神学或哲学语汇来阅读《忏悔录》,某个程度可以说违反了《忏悔录》的题旨[将圣经或教父着作当作「系统神学」的素材或是教义学资源,实为现代性之后的事]。
我们要谈论《忏悔录》的祈祷语式、回忆、爱、友谊、宽恕、哭泣、死亡、母亲、视觉、欲望、哀伤、离别、痛苦等作为我们思考的对象,还有一个显着的现象,《忏悔录》中大量地引述圣经,其中诗篇佔了极大的篇幅,为何祈祷与赞美有如此紧密的关系?
事实上,我们不应该期望、也无法得到问题的最终解答,理由是《忏悔录》这部书本身即是不断提问的过程,它探询的正是奥古斯丁理解自己不断生成、变化的事件,其中许多的遭遇和思考竟是些不确定性的东西,在祈祷之中向上帝开放他对事物的看法,同时也揭示他自身的无知。这是一种「祈祷的经济学」。
首先,《忏悔录》是一种通过回忆的方式去观看自我的过程。人如何观看自己?自我观看与一种忏悔的祈祷语式有何关系?事实上,观看作为一种生活,它开启了生活以外的各种可能,不管回忆作为一种观看的方式是否准确,但是对过去的回忆总是一种观看,一种「此时此刻」的、非语法或逻辑般的观看,甚至它与时间的关系变得模煳、变得难以理解。「时间」(X:17, 20)不正是经常被人拿来讨论《忏悔录》的主题之一吗(Paul Ricouer: Time and Narrative, chapter.1)?奥古斯丁对时间的困惑不是哲学性的,而是祈祷性的,不是通过论证,而是通过回忆。回忆是人的一种存在向度,正是这个从人的存在来理解时间、从忏悔的语式建构出来的时间意识,给廿世纪的现象学一个关键性的切入点[胡赛尔在《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中坦言其对时间意识的分析受到奥古斯丁的激发,甚至对《忏悔录》卷十一做过眉批和注释;海德格在1920–21年间开过一门讨论《忏悔录》卷十的研讨班,成了《存有与时间》的起源]。没有时间,就无需忏悔。
通过「记忆」,奥古斯丁的时间是一种「凝神」(intentio)的状态,是指人在自身又跃出自身的视域中看过去、现在与未来,因此过去、现在与未来不是静止的[这里的时间并不是胡赛尔的知觉意识经验的retention, intention, protention],而是「溢出」(ek-statische)的,但是这一切都在忏悔的意识中进行,所以是收摄心神、专注于上帝或永恆的一种「记忆现象学」。
《忏悔录》的书写之所以可能,正是依靠「记忆」这个活动,奥古斯丁把记忆看作是一种「影像」,而且这些「影像」是通过感官得到的(X:8)。相对于「记忆」,那就是「遗忘」,奥古斯丁自己问到:「遗忘究竟是什么?」(X:17)若遗忘,就没有记忆,但遗忘又是如何记起来的呢?我们真的忘记还是记起了某些东西?记忆究竟有多真实?值得注意,忘却并不是不存在,它仅仅是以沈默而非公开、非坦白的方式存在,记忆和忘却形成了忏悔的辩证,是关于「坦白与沈默」的辩证。人类似乎总是在记忆和忘却之间建构、摧毁,「解构」的思想正是对此「遗忘」产生兴趣开始(尼采、海德格、德希达),当然我们还想到「精神分析学」[弗洛依德晚年也写了一本忏悔录:《摩西与一神教》,这是一种经过现代性以后的书写方式,把自己隐身于巨大的迫害之下,企图抹除与自己任何相关的记忆,通过记忆的抹除,抹除身份,即抹除认同,即为现代精神分析学的另一种书写:为了忘却,而非记起]。
《忏悔录》最深刻之处即是存在着一个「我」:「但现在我在你面前,用这些文字向人们忏悔现在的我,而不是忏悔过去的我。」(X:3) 《忏悔录》努力呈现这样一个「我」:一个通过「忏悔」的方式来呈现一个「我II」,正是这个「我I」使这种活动得以进行,正如德希达说到:「一个画家考虑他自己,被吸引于、关注于那形象,然而那形象又在自己的眼前消失于深渊之中时,他绝望地试图再次捕捉自己的动作便已经是一种记忆的活动。」(Derrida, Memoirs of the Blind, 68)换言之,想要呈现的「我II」,正是那个「我I」,所以就必须不断地回忆,不是逼近于「我II」,当然也不是「还原」,关键在于它所展开的「视域」,是不是如李欧塔(Lyotard)所言的:「奥古斯丁是为了避免遗忘而书写,恰恰他所遗忘的正是自己。」(Lyotard, The Confession of Augustine, 83)。
记忆是一种源于上帝给我的,所以它是恩典而非人的能力,因为忏悔的记忆主要引自于「在你面前」(X:2, 17)。在上帝面前的我,通过了对现在的我的遗忘,记忆起过去的我;过去的我如此清晰不是源于过去,而是源于记忆起过去的我的「现在的我」,这个「现在的我」正竖立在「你面前」,一个我倾听祈祷和赞美的「你」的面前。
是我,又不是我,或者是另一个我。忏悔源于看到别人看不到,只有自己看到的罪恶,或不通过回忆就无法看清的我;坦白是为了获得宽恕,为了得到宽恕必须记忆起自己的过犯,无法记起的,就无法获得宽恕。要说出自己的罪(宽恕),必须承认自己的罪(忏悔)。
所以奥古斯丁说:「在你眼中,我对我自己是一个不解之谜,这正是我的病根」(X:33),我们通过奥古斯丁的书写发现,「忏悔」这种独特的语式正是一种「因为我(I)所做的,我(II)不知道」。基督教的忏悔意识恰好不在于「知道」自己的什么,相反的,犯错是因为「无知」,即是「不知道」。正是「忏悔」符合了其根本的含意:无知的犯错,所有的犯错即是出于这样一种无知,无知或不去知道都是一项罪,忏悔即是避免无知,尽管不知道,但必须坦白承认自己「无心之过」[「无心之过」仍是一种过错,而非现代「求真意志」的犯罪学之脱罪理由]。一切之过,莫过于「无心之过」,正因为此一「无心」而非「有意」,更说明了忏悔之必要,向着上帝忏悔而非向着自己「改过」。
三、
我们可以发现,《忏悔录》通篇都在唿求「主啊」、「我的上帝」这个专名,究竟这个名字代表了什么?为什么忏悔必须是通过我们唿求祂作「主啊」、「我的上帝」才是可能的呢?忏悔可以不唿求「主」的圣名吗?人向一个「名字」祈祷是如何可能的,尤其是这个「圣名」,忏悔之徒是如何认识到这样的「不可能性」,也许,向一个「名字」祈祷是可笑的,也是不可能的。而且,忏悔如果是为了激起我们对祂的爱、对祂的称颂(XI:1),我们对一个「名字」的爱和称颂意味着什么?什么样的「名字」可以成为我们去爱、去称颂的呢?为什么是「主」这个圣名而非别的?任何一种名字被唿唤,都代表着一种欲望,祈祷是一种「拯救圣名」(saving the Name),将「名字」给了悬置,它将我们的欲望搁置于悬而未决之中,这样的「主」是一切,也可以是空无,如德希达所言:「它总是离你而去,却又从不远离。」(Derrida, ‘Post-Scriptum,’ in On the Nam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上帝的名字,是一个「公开」的名字,不属于任何人「专有」的名字;上帝的名字,当我唿唤祂,通过祈祷的语言,祂成了我召唤「作为秘密的我」的上帝,一个属于我的「专名」(否定神学),所有的秘密系于此一「专名」中。因为在祈祷的语式中,「唿求」不是唿求某物「在场」[形上学],而是「给予」[神学],即作为礼物般的「给予」,一种满溢的到来[Jean-Luc Marion的礼物现象,with/out]。
上帝是一个拯救的名字(Sauf le nom),这是带上了否定神学印记的名字;上帝的名字并不是可以理解的东西,而是一个需要回应的名字。这即是祈祷中的「唿求」所带有的现象学意义。奥古斯丁对上帝的名字的唿求,不是唿求某物的「在场」,而是唿求相伴,在祈祷中,一种来自于「他者」的相伴,是对唿求的回应,也是对于「在场」的超越。
《忏悔录》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关于真理的问题。奥古斯丁在第十卷开头说到:「我愿意在你面前,用我的忏悔,在我心中履行真理;同时在许多证人之前,用文字来履行真理(facere veritatem, to bring forth the truth)」(X:1)这里注意到「书写」这个动作作为对「履行真理」的理解,而非被降低为认知理性秩序内的启示、解释、和告知,奥古斯丁想在书写中忏悔(in litteris, per has litteras)(IX:12, 33; X:3, 4),书写即是铭刻于将来的书写,书写不仅仅是对过去的书写,由于与记忆的问题有关,在已经发生的事上,通过记忆铭刻于将来,为此向教友们做见证。于是,书写、记忆、忏悔成了一种三位一体的关系,奥古斯丁的「真理」问题在此形成一种独特的书写形式[履行真理的独特语式。阿伦特在奥古斯丁那里发展了她的「行动哲学」]。
德希达说:「自画像者并不告诉人们什么,他只是承认自己的过错,并要求宽恕」(Memoirs of the Blind, 117)。上帝原已知道一切,因此忏悔并不是在告诉上帝任何事情,好像上帝不知情一般;任何的忏悔都意味着寻求「宽恕」过错,但是寻求「宽恕」的过程也是在此「过错」中,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即是表达了这样一种宽恕,但是,它并不是为了什么事情而求得的宽恕,而是一种不为任何事情而求得的宽恕。事实上,所有已然发生的事情都是无法挽回的,一切都已经过去,重提陈年往事似乎也于事无补,所以忏悔还是否必要?为了回忆的忏悔,或为了忏悔而回忆,表面上,奥古斯丁说了他许多犯罪的「事证」,正是他把记忆理解为此时此刻,所以,这些忏悔的情节要是成立,其唯一的可能性即在于「无法被宽恕」,一切的忏悔都是指向这样一种「宽恕的不可能性」,以及真正的「宽恕」即是「宽恕那不可宽恕」的[德希达]。可见,奥古斯丁所有的忏悔和「犯罪事证」,并非直指事物本身,一切都在「延异」中产生了其他可能的含义,这是奥古斯丁最为推崇的「寓意解经法」(林前3:1–6),这种方法应用于祈祷之中最为明显和直接。
全本《忏悔录》运用着圣经的「寓意」手法,都是一种在给定的意义中寻找其他可能性,这里也引伸出《忏悔录》暗示着处处充满着「不可靠性」,忏悔很难不成为某种「欺骗」,「公开的欺骗」,因为连奥古斯丁本人都觉得「我无法证明我所言的真假」(X:3)。这里的意思至少表明三方面:说出的不一定是真的、说出真相是不可能的、我只是在履行真理。
正是如此,忏悔意味着是一次又一次地暴露自己无可救药的犯错,必须说出而非不说,不是无法说出,而是不知说些什么是适切的或恰当的,说出之后并非供人歌颂和赞许,因为忏悔更多是一种自我解构,自我只能通过「他者」来呈现,自我永不是「同一性」的,因为任何的欺骗最难克服的即是自我欺骗[也是笛卡儿最难对付的「怀疑」:恶魔论论证],否定自我欺骗的存在就必然是一种「悖论」,所以这是一种无法克服的「欺骗」,正是这种再一次的犯错为我们打开另一种可能性的条件,如果我们并不是克服「欺骗」而通往真理,奥古斯丁等于是「公开说谎」的人,其本身即是「带面具说话」的人,往往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正是「隔着某物」说话(参见尼采〈真理与谎言之非道德论〉),祈祷的状态即是一种「隔着某物」在说话的方式。
事实上,《忏悔录》卷十是作为一至九卷的「前言」或「导言」,奠定了我们对于全本《忏悔录》的思考与理解。《忏悔录》卷十分两个部份,8节至29节论及「记忆」,30节至42节谈到「感官」,说明了身体的活动可分作两部份:记忆与感官,忏悔不是通过感官而是记忆,这里虽然有柏拉图思想的影子,但不是认识论的而是祈祷的。由于祈祷本源地来自于回忆,没有回忆,祈祷就不可能。记忆,作为事实本身,包含了「忘却」,「忘却」在此恰好是指某种已然存在的东西,回答忏悔之可能性即在此;忏悔即是回忆,回忆之具体内容恰恰好所指的正是身体的活动。
《忏悔录》中有关「身体告白」也是一个有趣的题目,这个问题当然是因为傅柯「主体诠释学」和「性史」所引起的。奥古斯丁通过了「身体的活动」(诱惑、好奇心、贪心、虚荣、同情……(X:30–42))来进行忏悔,「身体」在忏悔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被当作否定的对象,同时却又是一种「发现真相」的途径,而且奥古斯丁对于上帝的赞美又避免不了使用身体可以感觉的方式来「体验」上帝(XI:1) (X:27),到底身体与忏悔的体验有何关联?「爱上帝」如果不是一种欲望使然,那又是什么?身体为何如此的神秘,以至于成了与「爱上帝」对立的东西?可见,在忏悔的身体告白中,身体有多神秘,上帝就有多神秘。
傅柯把忏悔理解为一种古老的思想,它贯穿着整个西方思想史,以「关心自己」为实践方式,一方面使自己成为对象,一方面则是将自我技术化,前者将注意力朝向自己与非利己主义形成悖论,后者即是以自我规训的方式达到自我控制和改变自己(Foucault,《主体解释学》,12)。「忏悔是一种说话行为,主体通过忏悔在证实自己是什么时候与这种真相联系,置身于一种依附他人的关系中,同时又改变他与自身的关系」(《主体解释学》,386),所以忏悔与身体、爱欲、真理、自己(auto)、说真话等有关。
傅柯分析parrhesia这个拉丁字「坦白」的意思时发现,这个字还有libertas(自由)的意思,是开放让人说话、说出他需要说出的话、说出他想说出的话,它意味着说话主体的一种道德品质的要求(《主体解释学》,381, 389)。我们不能忘记奥古斯丁这位「修辞学教授」的身份,「修辞」在此并非指一种文学或说话的技巧,它更多的是一种与自我认识和自由有关,因此,如何通过这种语言的训练来达到对主体的技术化正是《忏悔录》最隐蔽的问题,这与祈祷和修身这种宗教生活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忏悔意味着在上帝的注视底下,内心世界的时间被现在激活,对过去的自己进行述说,以作为皈依上帝的见证。《忏悔录》不断地讨论眼睛,不管是「流泪的眼睛」、「目欲」(犯罪的看)或「无形的眼睛」(信仰的真光),隐身在这一切背后最巨大的眼睛即是「上帝的眼睛」,这才是形成忏悔意识,以及使忏悔得以可能的根本条件。因此「我非但不能把我隐藏起来,使你看不见」,「不论我怎么样,我完全坦露在你面前」(X:2),正是一切在祂的鉴临之下变得无所遁形,忏悔也就变得「不得不」。
尼古拉库萨(Nicholas of Cusa)说「上帝就是眼睛」,关于我的存在与上帝的凝视,他做了极为经典的表达:「所以我存在,因为你在观看着我;倘若你把自己的视线从我身上移开,则我将不能存在。」[《论隐秘的上帝》,89,76]忏悔即是源于上帝的观看,「眼睛所至,便是爱之所致」,上帝凝视着我,上帝的目光是爱的目光,因此祂的观看就是爱[《论隐秘的上帝》,76,87]。凝视即关爱,而非「他人即地狱」。
奥古斯丁说:「我爱上帝,是爱另一种……。」(X:6)以上种种的说明,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奥古斯丁在《忏悔录》所讲述的是一个人的故事,但是,那是一个关于他自己成为了一个问题的人(I am become a question to myself)的故事。奥古斯丁正讲述着「另一个我」(X:30)吗?是他本人,抑或上帝?
四、
严格说来,《忏悔录》到卷九就结束了,即结束于母亲去世的事件上,可能《忏悔录》的写作真正的起源来自于莫妮卡之死。《忏悔录》也是通过母亲的死亡来哀悼自己的过去,所以莫妮卡的死是一个关键,由她引起了奥古斯丁对所有过去的追忆,《忏悔录》即是向上帝的忏悔也是向死去的母亲的忏悔。母亲与奥古斯丁的亲密关系遍满于《忏悔录》每个细节中,母亲的存在宛如上帝在世的代表,一切使奥古斯丁转向上帝的关键都来自于母亲的祈祷、母亲的哀伤和焦虑,母亲的逝世使他顿时失去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源于母亲。卷九第十节即一个神秘的「奥斯蒂亚经验」(IX:10),这是奥古斯丁与母亲离别前最为深切的交谈经验,一种真正的「永别」,尽管无数次都是奥古斯丁别离了母亲,这次却是母亲与他道别,而且是「永别」。因此是母亲引发他的忏悔,引发对过去的追忆,通过追忆作为与过去一切的「永别」,值得注意的是,那是他接受洗礼后不久就发生的事,那年他三十三岁,莫妮卡最后是了无遗憾般地与奥古斯丁永别了。
《忏悔录》是一本哀悼母亲死亡之作,真正的关键是母亲的死。[59岁的德希达在尼斯面对着垂死的母亲Georgette Safar Derrida,仿傚了奥古斯丁写下了五十九章自传体的独白:Circumfession《割礼告白》。德希达在奥古斯丁大街长大,这是以他的同乡名字而取的。德希达公开了他的身份和信仰:他是最后一位犹太人,道出了自己真正的名字Jackie,以及一直以来旁人都不曾知道的名字Elie,这属于母亲给予他的生命,一个礼物的记号。这位「渺小黑皮肤的阿拉伯犹太人」流着眼泪对我们说:我在祈祷和眼泪中公开了秘密,要他人在阅读他的书时望到他的眼泪,让他们知道我的一生是在一连串漫长的祈祷中度过。Circumfession, 38–39, 83–84]《忏悔录》写于母亲逝世十年之后,也是他正式当上希波大主教的第二年,人生走到如今,《忏悔录》作为告慰天上母亲的灵魂,也许是奥古斯丁最大的动力所在,还有什么比母亲对他的影响更加巨大呢?还有什么比母亲对他事奉上帝一事更为操心呢?《忏悔录》全书处处「流着泪」祈祷,宛如母亲为他所流的泪一般。
毫无疑问的,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一部告诉我们关于「眼睛」的史前史的着作,忏悔意味着「看见光」,但他指出的例子中,竟是一群「失明」的人,包括多比[一个失明的多比是如何教诲他的儿子多比雅]、以撒[以撒在盲目的情况之下将祝福给了对于祝福做出选择的雅各]、雅各[这些人都在奥古斯丁的书中出现过,但他似乎忘了保罗也是失明的],上帝打开了他们那双「无形的眼睛」(invisible eyes)看到了「真光」。(Memoirs of the Blind, 117–119)这是一种盲者独有的视域,只有他们才「用对」了眼睛,看到应该看的东西,即上帝。
奥古斯丁祈祷说:「我的心如何向你哀号,我的眼睛如何热泪盈眶」(X:37)。德希达认为《忏悔录》是一部「眼泪的书」,我们可以在书中处处找到流泪、哭泣、哀哭的经验。(Memoirs of the Blind, 126. [德希达还要我们「看,这个人」(Ecce Homo):尼采,特别是他在杜林抱着马哭泣的那轶事]) 眼睛无法看到自己,眼睛在流泪的时候证实了这件事;眼睛失去了凝视作用,开启了它更多的可能性。所以说到底,忏悔绝非自己看见自己,柏拉图说明了眼睛必须看着一个客体,通过看着它,眼睛才看到自身。这是一双「他者」的眼睛,它不是我自己的眼睛,一旦眼睛看向他,就将看见自己在看[如拉冈的「镜像」]。由于眼睛无法看到自己,这种自我观看,正是看到我是盲目的或瞎眼的。
德希达说他流泪时,他不知道究竟是自己还是母亲在哭泣,不同于海德格在《存有与时间》的「死亡」是自己的死,德希达面对着母亲,是他者的死,他者的死正是我的死,是一种给予,正如泰勒(Mark Taylor)所言的‘(m)other’。所以,说奥古斯丁流泪,不如说是莫妮卡的眼泪,是莫妮卡的流泪与祈祷换得了今日「喜悦的泪水」。哭泣是一种「失明的状态」[据说圣法兰西斯因流泪过多而失明],眼泪是盲目经验表现的最高形式。眼泪是只有女性[Monica/Georgette]能以保持盲目所提供的「视域」,如德希达所说:「眼光的实质不是视力而是眼泪,……揭示性或启示性的盲目,那显露了眼睛的真真实实的盲目,是为眼泪遮蔽的凝视。」「当泪水遮蔽了视力的那一刻,它们揭示了眼睛真正的功能。……眼睛的终极目的是使视力探寻而非观看,关注祈求、爱、欢乐或悲伤而非打量或凝视。」(Memoirs of the Blind, 126–127。参见耿幼壮《圣痕》第五章)
如果《忏悔录》的祈祷和眼泪即是对于母亲的哀悼,同时也在哀悼自己,那么,母亲的死与自己的死是否为同一件事,由于过去充满着母亲的回忆,伴随着母亲的死去,也带走他的过去,是要忘记母亲还是忘记自己的过去,奥古斯丁是向母亲和过去的自己道别,抑或是重新记起这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读《忏悔录》这本著作,总能勾起我很多复杂的情绪。第一次认真拜读,是在我人生一个比较迷茫的时期,当时正值壮年,事业似乎有些起色,但内心却总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我尝试去阅读很多哲学著作,希望能找到一些指引,而《忏悔录》恰好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当时是被它那充满戏剧性的标题所吸引,想着一个圣人,怎么会有“忏悔”这两个字?读进去之后,我才明白,所谓的圣人,也曾是凡人,也曾有过迷失。奥古斯丁的文字,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他毫不避讳地描绘自己年轻时的种种过错,那种坦诚,让人动容。我特别喜欢他描述自己对知识的追求,那种渴望理解世界、理解真理的冲动,和我当时的感受非常契合。他从怀疑论到接受基督教信仰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充满了艰辛的探索和内心的斗争。这让我觉得,信仰并不是一种盲目的服从,而是一种深刻的个人旅程。书中那些关于时间、关于记忆的哲学思考,也让我驻足良久。他如何解析时间流逝的本质,如何反思记忆对个体身份的影响,都让我看到了一个思想家深邃的洞察力。对我来说,《忏悔录》不仅仅是一本宗教典籍,更是一部关于人类精神成长、关于如何与自我和解的伟大作品。
评分《忏悔录》这本书,对许多在台湾生活过的朋友来说,肯定不陌生。我最早接触它,大概是大学时期,那时候觉得奥古斯丁这个人,怎么会有那么多挣扎、那么多内心的对话?整本书读下来,感觉像是他把灵魂赤裸裸地摊开在你面前,让你看尽他的矛盾、他的追寻,还有他那颗渴望救赎的心。当时的自己,年轻气盛,对人生还没有太多深刻的体验,所以读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旁观者的角度,觉得他写的那些罪恶、那些诱惑,离自己还很遥远。我记得特别清楚,有几次读到他描述年轻时沉溺于感官享乐的部分,还会有点替他感到不解,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性的弱点?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再回头看这本书,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再读,我更能体会到那种“爱之晚矣,而恨之切”的痛苦,那种明知不该,却又无法自拔的挣扎。尤其是在面对人生的重大选择,或者是在人际关系中遇到困境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奥古斯丁在书中那些诚恳的自省。他那种对真理的极度渴求,对信仰的坚定追求,以及最终找到平静的历程,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本书不只是一个人的人生记录,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模样。
评分要说《忏悔录》这本书,对我而言,它不仅仅是一本阅读材料,更像是一段精神上的旅程。第一次翻开这本书,是在大学毕业没多久,那段时间正是我对未来感到迷茫,对人生价值感到困惑的时候。我从小接受的是比较传统的教育,对西方哲学和宗教的了解非常有限,所以一开始读的时候,觉得奥古斯丁的很多叙述都有些晦涩。但他那种对自己过往人生毫不掩饰的剖析,却深深吸引了我。他坦诚地描绘了年轻时对情欲的沉迷,对物质的追求,以及在思想上的种种误区。我记得其中有一段,他描述自己如何被虚荣和荣誉所驱使,这让我反思自己当时在工作和生活中,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虚荣心在作祟。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母亲莫尼加的形象,她那种坚定不移的信仰,那种对儿子无私的爱和期盼,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坚持和祷告,最终成为了引导奥古斯丁走向正轨的重要力量。这本书让我明白,人生的道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会有很多诱惑和曲折,但最终能否找到方向,取决于内心的坚持和对真理的追求。这本书给了我很多关于如何面对内心挣扎的启示。
评分《忏悔录》这本书,在我人生不同阶段阅读,总会品味出不同的滋味。年轻的时候,读它,更多的是被奥古斯丁那段传奇的生命故事所吸引。他从一个放荡不羁的青年,最终成长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神学家,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转变。我尤其对他在母校罗马接受的教育,以及后来在迦太基求学的经历印象深刻。他所描绘的那个时代的学术氛围,以及他对知识的饥渴,都让我感受到那个年代求知者的精神风貌。他书中那些关于修辞学、哲学辩论的描写,至今仍然让我觉得生动有趣。我当时对基督教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所以他对宗教的怀疑、对教会教义的困惑,以及最终被福音所吸引的整个过程,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新颖的。他那种对真理的不懈追寻,那种在思想和情感上的拉扯,让我觉得非常真实。我记得他提及自己和莫尼加的母子情深,还有母亲为了他的信仰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那部分描写总是让我感动。这种跨越时空的亲情和信仰的连接,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更多的是在故事层面去理解这本书,还没有完全领悟到它背后更深层的哲学和神学含义。
评分《忏悔录》这本书,每次读都会有新的体会,它就像是一坛老酒,越品越有味。我第一次接触它,大概是在二十多年前,那时候在台湾的图书市场,这本书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对我来说,它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我被书名所吸引,一个圣徒,为何要“忏悔”?这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读进去之后,才发现这本书的深刻之处。奥古斯丁的文字,有一种直击灵魂的力量,他毫不避讳地揭露自己年轻时的罪恶和迷茫,那种坦诚,是极其罕见的。我尤其被他对时间的哲学思考所打动,他如何剖析时间的短暂与永恒,如何解读记忆在塑造个体存在中的作用,都让我受益匪浅。他从一个怀疑论者,到最终皈依基督教的过程,充满了艰难的探索和深刻的内省。书中关于他与朋友之间的交往,以及他对知识的渴望,都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探索者的丰富内心世界。他与母亲莫尼加之间的深厚情感,以及母亲对他信仰道路的深刻影响,更是让我看到了信仰传承的伟大力量。每一次重读,我都能从中找到新的共鸣,新的启示,它让我对人生的意义,对信仰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