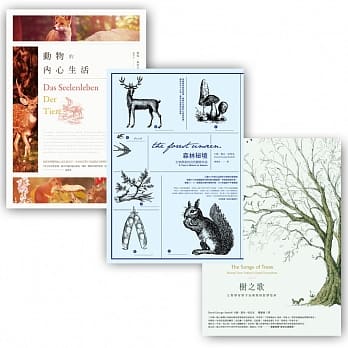具体描述
《华尔街日报》年度最佳科学书
《科技时代》年度最佳科学书
趋势科技版的《如果这样,会怎样?》
意想不到的未来,就在眼前!
未来,这世界到底会变成怎样?
为什么距离首次登月已经这么久了,我们还没有在月球上建立殖民地?
为什么许多我们期盼已久的科技,还没有成真?
《拯救或毁灭世界的十种新创科技》带你预见未来,
细数十种众所瞩目的发展中新兴科技,
例如上太空要如何变便宜、我们要如何利用太空资源、
医学会不会走到为个人量身订制的境界、
3D列印有没有可能解决器官移植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为大脑编写程式,让自己更聪明?
作者用逗趣的漫画与幽默的解析,
说明这些科技目前进行到哪里,
它们绕了哪些冤枉路、走了哪些死胡同,
怎样会把这世界搞得一塌煳涂,
怎样才可能让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著者信息
凯莉‧韦纳史密斯Kelly Weinersmith
美国莱斯大学生物科学系兼任副教授,她研究的是操弄宿主行为的寄生虫。她除了是一流的研究者,还主持了一个全美排行前二十名的热门科学播客「科学有点是」(Science……Sort Of)。她的研究也在《科学》、《自然》等期刊。
查克‧韦纳史密斯Zach Weinersmith
知名网路漫画家。他的第一个学士学位读的是文学,但在开始画漫画之后,对科学产生了兴趣,于是回到大学取得物理学士学位。他有一个颇受欢迎的冷笑话漫画网站「周六早晨的麦片粥」(Saturday Morning Breakfast Cereal),作品散见于《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等媒体。
译者简介
黄静雅
台南市人,台湾大学大气科学硕士,着有《台湾天气变变变》(合着),译有《看云趣》、《观念地球科学》(合译)、《地震与文明的纠缠》、《大口一吞,然后呢?》、《第六次大灭绝》(荣获第八届吴大猷科普翻译类佳作)、《如果这样,会怎样?》、《勇往直前》。
除了大气科学专长,也曾出版音乐专辑「看月娘」、「生活是一条歌」;创作儿童音乐专辑「春天伫陀位」及「幸福的孩子爱唱歌」等。
2002年之后定居加拿大温哥华,却心系台湾的一举一动,自称是「用母亲的眼睛与关怀万物的心,跨界地球大气与原创音乐」的家庭主妇。
图书目录
第一篇 预见未来的宇宙
1. 太空旅行可以更便宜吗?:征服最后疆界的代价,实在贵死了
2. 小行星採矿:尽情搜刮太阳系的废物堆
第二篇 预见未来的事物
3. 核融合能源:太阳的能源就是这么来的,但它能用来烤面包吗?
4. 可程式物质:如果你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变成你的任何东西,那会怎样?
5. 用机器人盖房子:金属仆人,给我盖一间房子!
6. 扩增实境:操纵现实的另一种选择
7. 合成生物学:有点类似《科学怪人》,不过怪物从头到尾都在尽心尽力的炼药和工业投入
第三篇 预见未来的你
8. 精准医学:你的种种毛病都可以用统计学方法对症下药了
9. 生物列印:要是可以列印新的肝脏,为什么才喝七杯玛格丽塔酒就不喝了?
10. 脑机介面:你需要它,因为即使经过四十亿年的演化,你还是不记得把钥匙放在哪!
结语:这些科技恐怕还要再等等――失落章节之墓
图书序言
预测未来的书很多,这本书是其中之一。
幸好,预测未来挺容易的。人们一天到晚都在做预测。做出准确的预测倒是比较难一点,但是坦白说,真的有人在乎吗?2011年有一项研究叫做「名嘴是不是在唬烂」,评估二十六位专家的预言能力。预言能力的等级从「料事如神」到「老是摃龟」。
对大多数人来说,阅读这项研究的乐趣,在于发现某某人不但是蠢到不行的蠢蛋,而且是「统计学算出来的」大蠢蛋。以我们这些科普作家的角度来看,这项研究还有一项令人格外激动的结论:不管这些名嘴的预言造诣如何,他们到现在都还有工作。事实上,最差劲的预言家中竟然有很多是最知名的公众人物。
如果预言能力与功成名就,两者确实扯不上关系,我们的立场已经稳如泰山了。毕竟,那些专家只是想揣测「争吵不休的一小群政治人物,短期内会惹出什么麻烦」而已。他们并不想决定:五十年内会不会出现上太空的「天梯」;我们会不会把脑子里的东西上传到云端空间;机器会不会帮我们印出新的肝脏、肾脏、心脏;医院会不会利用游来游去的微型机器人来治病。
坦白讲,本书提到的科技,到底会不会在特定的时间点实现它们最完整的面貌,实在难以奉告。新科技并不只是「慢慢累积愈来愈厉害的事物」而已。雷射和电脑等科技大幅度的飞跃突破,往往有赖于不同领域中彼此不相干的研究发展。就算有了这些重大发现,特定的科技会不会找到市场也没人说得准。没错,来自1920年的时光旅人,我们有飞天车。错了,没有人想要这种车。它们是「西洋棋拳击」式的载具 —偶尔看看还挺好玩的,不过多半的时间,你宁可不要一心二用。
考虑到我们为大家做的预测很可能不但不准,而且还很蠢,我们决定要採取一些策略,那是我们在拜读其他作者的预测未来书籍时学来的。
第一步,先做几个初步的预测:
我们预测电脑会变得更快。我们预测萤幕解析度会变得更高。我们预测基因定序会变得更便宜。我们预测天空还是蓝的,小狗还是很可爱的,馅饼还是很美味的,乳牛还是不停的哞哞叫,装饰用的擦手巾还是只有你妈妈会在意。
请大家过几年再回头检验,看我们的预测准不准。注意喔,我们并没有预测具体的时间点,所以选项只有「准」或「没有不准」两种。
我们已经做完第一阶段的预测了,现在准备再接再厉。我们预测未来二十年内,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可望降低火箭发射成本达30% ∼ 50% 。我们预测未来三十年内,验一次血可望诊断出大多数的癌症。我们预测未来五十年内,奈米生物机器可望治好大多数的遗传性疾病。
好,这样总共是十一项预测。我们认为,如果十一项有八项料中,我们就应该被封为天才。喔对了,假如第一组当中有任何一项成真,你们就可以洋洋洒洒写篇新闻稿,标题像是「预言基因定序之未来的夫妻档说,太空旅行在不久的将来会很便宜」之类的。
准确预测未来很难。真的很难。
新科技从来不是孤僻天才异想天开想出来的。时间久了,这句话更是愈来愈有道理。特定的未来科技不知有多少中间技术需要事先开发出来,而且很多中间技术在一开始发现时,似乎无关紧要。
有一项最新开发的设备,称为超导量子干涉仪(SQUID),我们会在本书中加以讨论。这种设备非常灵敏,可侦测脑部的细微磁场,这么一来,分析人们的思考模式就不用在脑袋瓜上钻洞了。
这东西是怎么来的?
嗯,超导体是任何「可在不耗电的情况下导电」的材料,跟以往的普通导体(例如铜线)不一样,普通导体的导电效果相当好,但是中间会耗掉一些电。
会发明超导体,是因为两百年前左右,法拉第正在制造某种玻璃器皿时,意外的把某种气体包入玻璃管中,而管里的压力竟使气体变成液体。那时候连电视都没有,所以维多利亚时代有一群人对气体液化的概念非常兴奋。
结果发现,要液化气体,冷却比加压更有效。科学家领悟了这层道理,着手开发先进的冷却技术,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办法液化顽强的气体元素,比如氢气和氦气。而且一旦有了液态氢或液态氦,你高兴冷却什么东西,几乎都可以利用它们来冷却。
举例来说,氦气在液态时约为摄氏 –232.2 度,如果你把液态氦倒在任何东西上面,氦就会变成气体并带走热量,直到你正在冷却的东西也达到摄氏 –232.2 度左右为止。
后来科学家很想知道,把导体的温度降到很低时会发生什么事。导体冷却时往往变得更容易导电。简单的说,这是因为导体有点像是电子的管路,但它们并不是完美的管路。以铜线为例,铜原子是会阻碍电子运动的。
我们所谓的「热」,其实只是原子层的急速晃动。加热(也就是晃动)铜线中的原子时,原子较会阻碍电子往下游移动,这道理就像是:开车时,如果前面的家伙一直变换车道,你要一路开到底就比较难。在原子层面,晃动(也就是加热)意味着电子较容易撞到铜原子,于是原子晃动得更厉害。这就是为什么笔电充电器用了一段时间后,会变得很热的缘故。
把液态氦放在导体上,铜原子的晃动能量就会转移给氦原子,然后氦原子就飞走了。现在铜原子比较不晃动,电子受到的阻碍少了很多。温度愈低,电子愈容易流动。
当时有个争议:如果铜原子趋近于不晃动会怎么样?有人认为电导会停止,因为在那样的温度下,连电子也动不了。有人认为电导会变得非常好,但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所以研究人员开始把超低温液态气体倒在金属元素上。这下可好,有些金属达到一定的超低温时,竟然变成完美导体(也就是超导体)。如果让金属保持冷得足以超导的温度,就可形成循环不已的电流回路。这或许听起来像是有趣的科学新知,但这会导致各种不可思议的怪事!那样的循环电流会产生磁场,这表示你可以把这些冷金属变成永久磁铁,磁力强度则取决于你加了多少电流。
后来到了 1960 年代,有个叫约瑟夫森(Brian Josephson,曾获诺贝尔奖,但目前他在剑桥大学一天到晚捍卫冷融合和「水记忆」之类的旁门左道)的家伙,发现超导体的某种配置方式,可侦测磁场中的细微变化。这个装置称为约瑟夫森接面,因为有了这个接面,最后才能开发出超导量子干涉仪。
就这样,说完了。想想看:假如两百年前有人问你,怎样才能打造设备来扫描人的脑部型态,你难道会马上回答:「好,首先要在玻璃管子里装一些气体」?八成不会。事实上,连最后一道重要技术步骤(约瑟夫森接面,重申一下,发现这道步骤的人认为「水记得你丢入的东西」是有可能的)首度提出时,也被认为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它的性能所利用的理论架构,是法拉第死后很久才发展出来的,稍后我们会加以解释。
科技发展的偶然性,正是我们为什么没有月球基地的原因,尽管我们认为早该有了,但我们有袖珍型超级电脑,这倒是很少有人料到。
本书提到的所有科技都面临同样的难题:我们能不能打造天梯上太空,可能取决于化学家把碳原子排列成小细管的能耐有多强。我们能不能随心所欲制造任何形状的物质,可能取决于我们对白蚁的行为有多了解。我们能不能打造医疗用的奈米机器人,可能取决于我们对于折纸的理解程度有多好。说不定,到头来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派得上用场。历史未必会一再重演。
我们现在知道,古希腊人会制造复杂的齿轮系统,却从未建构先进的时钟。古亚历山大人拥有初步的蒸汽机,却从未设计火车。古埃及人四千年前发明了折叠凳,却从未创立IKEA。
总归一句话: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什么时候才会发生。
那干嘛写这本书?因为每天随时随地都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而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还有人变得愤世嫉俗,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早就该有核融合能源,或是可以在週末来趟金星之旅。这种失望,可不能老是怪在对未来「画大饼」的科学家头上;与本书类似的书籍,往往忽略了我们与小说描述的未来之间,存在的经济与技术挑战。
我们不知道那些书为什么总是漏掉这些挑战。假如上月球轻而易举,阿波罗 11 号的故事会更精采吗?在我们看来,脑机介面的概念之所以如此令人心动,部分是因为,我们目前对于如何解读人心思维几乎毫无线索。有无穷无尽的问题等着问,许多事物等着发现,无上荣耀等着争夺,无数英雄等着锦上添花。
我们选出十大新兴领域炫科技来和大家一同探索,大致上从大排到小,从外太空、到庞大的实验性发电厂、到打造事物及体验世界的全新方式、到人体,最后一路到你的大脑。无意冒犯,请勿见怪。
我们对于每个章节的指导原则是,如果你去泡酒吧,有人问你:「喂,核融合能源是怎么回事?」你能提供的最佳答案是什么?有人说,我们根本不知道酒吧长什么样子,但重点是每一章都会告诉你,某某科技是什么,目前进行到哪里了,实现这项科技的挑战是什么,怎么样可能会一塌煳涂,怎么样可能明天会更好。
对我们来说,科学进步令人兴奋,并不是因为科学「帮我们做新的事情」。而是了解「去小行星挖矿」或「用一大群机器雄兵盖房子」有多困难,才使科学变得更有趣。意思就是说,当这些事情终于真的发生,你就会明白到底科学进步会多令人兴奋了。
对于科学技术绕了哪些冤枉路、走了哪些死胡同,你也会略知一二。我们在大部分章节的结尾,会把挖掘出的一些怪诞(或恶烂或很赞)的小点子「报乎你知」。这些部分有时与本身的章节直接相关,有时只是一些很扯的东西,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碰到的。真的是很扯,比方像是「玉米面包制成的章鱼」那么扯。
为了这所有的章节,我们必须拜读一大堆科技书籍和论文,还得跟一大堆有点疯狂的人打交道。有些人的疯狂程度比较严重一点,他们通常是我们的最爱。进行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共通的经验,那就是我们对于每个主题的先入为主观念,全都给毁了。我们在研究每个案例时,才发现我们不单是不了解技术本身,而且也不了解它受到什么样的阻碍。看似复杂的东西往往很简单,看似简单的东西却往往很复杂。
新科技是很美妙的东西,正如米开朗基罗的《圣母怜子》或罗丹的《沉思者》雕像,往往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创造出来。我们希望大家不但了解科技是什么,而且了解未来为何如此顽强的抗拒我们的苦心。
写于韦纳史密斯庄园, 2016 年 9 月
P.S. 对了,我们也希望大家知道这个实验:大学生被迫用一边鼻孔唿吸,然后进行测验。这有点扯得上关系。我们保证。(摘自本书前言)
图书试读
新肝脏列印就有,让我们干杯吧!
想像有一天你一觉醒来,感觉疲惫不堪而且很想吐。等终于吐完了,你照照镜子,发现眼睛和皮肤有点黄黄的。你把儿子叫来,他赶紧开车送你去医院。几个小时后,你的医生进来,脸色凝重。你需要新的肝脏。
「嗯,」你心想,「找个肝脏会有多难?我认识的一大堆人都有肝脏。」你瞧瞧护理师。不行⋯⋯太小了。你瞧瞧医生。不行⋯⋯太老了。你瞧瞧你儿子,眼神一亮。他摇摇头。
「老爸,我小时候打少棒时,你如果多来看几场⋯⋯」
所以你走投无路了,只好加入等候器官移植名单,名单上目前有十二万两千多人。不过,你运气很好,排队等候肝脏的只有区区一万五千人。
根据你的所在位置、健康情形、年龄等因素,可以预期的是,你等候的时间少则数月、多则三年。通常肝脏会先给病情最危急的人,这代表你可能要等到病情从「很糟」变成「糟透了」,才能获得优先权。而且不行!不准为了早一点得到肝脏而拚命喝酒。
名列器官移植名单,不一定代表你会及时得到肝脏。美国每年有八千位等候器官的人死亡。不过,假设你是家境富裕的美国人好了。你肯定有更好的选择。你可以成为医疗观光客去其他国家,付钱叫陌生人把部分的肝脏「捐赠」给你。
你可能要考虑一下肝脏是哪里来的。或许你根本不用考虑。比方说,如果你去中国,你的肝脏可能是来自被处决的死刑犯。
即使你能接受器官买卖的观念,而且知道器官是人家自愿捐赠的,那你可能要想一下,如何定义「自愿」。有证据显示,在这样的体系里,最常见的器官捐赠者都是指望还清债务的穷人。通常这些人得到的报酬会比当初讲好的还少,而且到最后反而会更穷,因为他们的工作时数变少了,或是因为拙劣的手术影响了健康。
所以你又回过头来找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乞求他们施舍一点肝脏。肝脏具有相当神奇的再生能力,所以你不需要整个肝脏。「拜託啦,」你说:「只是一小块肝脏而已嘛!」
在你对自己二十年前错过一场重要的少棒赛表示由衷的悔意之后,你好不容易说服你儿子捐赠。结果,你发现他和你不相容。哈!所以你没去看那些少棒赛是对的。道歉收回。
用户评价
這本書名聽起來就像是硬科幻的經典開場白,那種既令人興奮又帶點不安的感覺。我想,現代社會最令人著迷,也最讓人擔憂的,就是科技的快速迭代。從人工智能、基因編輯,到太空探索、能源革命,這些名詞聽起來就充滿了無限的可能性。我特別好奇,作者將會聚焦在哪些具體的科技上?是那些已經在我們生活中嶄露頭角的,像是大數據分析、物聯網,還是那些聽起來更為前沿,甚至有點遙不可及,例如可控核融合,或者更進一步的,意識上傳?每一個新創科技的背後,都可能牽涉到倫理、道德、社會結構,甚至是人類存在的意義。我很期待書中能對這些複雜的議題進行深入的剖析,並且提供一些具有前瞻性的觀點。畢竟,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很難不被這些新興科技所影響,了解它們的潛在影響,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對於我們每一個人都至關重要。這本書或許能提供一個思考的框架,讓我們更理性地看待科技的發展,並且為我們未來的選擇提供一些啟示。
评分「拯救或毀滅世界的十種新創科技」,光是這個書名,就讓我聯想到許多經典的科幻電影情節。我在想,作者是不是會列舉出那些,一旦失控,就可能導致世界末日的技術?像是能夠操縱天氣的武器,或者能夠製造出無法控制的超級病毒的生物科技。但同時,我也希望書中能夠平衡地探討,這些科技是如何被設計出來,又是如何被期望來解決我們當前面臨的各種危機的。像是如何透過先進的材料科學來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或者如何利用基因工程來根治絕症。我特別喜歡那種,能夠將複雜的科技概念,用清晰、生動的方式呈現出來的書籍。我希望這本書不會只是羅列一些技術名稱,而是能夠深入探討每個技術的運作原理、發展歷程,以及它在不同情境下可能產生的影響。而且,我更期待的是,作者能夠引導讀者思考,我們作為人類,應該如何去監管、去引導這些強大的科技,確保它們真正為人類服務,而不是成為毀滅的工具。
评分哇,光是看書名就覺得超吸引人的!「拯救或毀滅世界的十種新創科技」,這個主題真的太有想像空間了。我一直對科技發展如何影響我們的未來感到好奇,畢竟科技進步的速度有時候快到讓人有點跟不上,但又不得不承認,許多過去只存在於科幻小說裡的技術,現在都一步步變成現實。這本書的標題直接點出了科技的兩面刃,既能造福人類、解決許多全球性的難題,像是環境污染、疾病等等,但同時也潛藏著巨大的風險,如果應用不當,後果不堪設想。我特別期待書中能夠深入探討這些科技的原理、發展現況,以及最關鍵的,它們可能帶來的各種可能性。畢竟,了解這些潛在的影響,才能讓我們更清楚地知道該如何應對,如何在科技浪潮中找到最有利於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方向。我希望作者能夠用淺顯易懂的方式,帶領讀者一同思考,讓我們不只是被動地接受科技的改變,而是能主動地去駕馭它,讓它成為我們走向更美好未來的助力,而不是走向毀滅的催化劑。光是這個標題,就已經讓我迫不及待想翻開了!
评分這本《拯救或毀滅世界的十種新創科技》,光聽名字就覺得是那種能讓人廢寢忘食的書!我一直覺得,科技的發展就像是一場賭局,有時候我們以為自己抓住了機會,結果卻可能玩火自焚。所以,我非常想知道,作者將會選出哪「十種」新創科技?是那些已經在改變世界的,例如無人駕駛、區塊鏈,還是那些更具顛覆性,甚至可能改變人類社會形態的,像是量子計算、腦機接口?我對這些技術的潛在影響感到極度好奇,特別是它們可能引發的倫理爭議和社會變革。書中是否會探討,當這些科技變得無比強大時,我們應該如何確保公平性?例如,當基因編輯技術成熟,是否會加劇社會階級分化?或者,當人工智能擁有自我學習和進化能力時,我們又該如何定義「意識」和「權利」?我希望能從書中獲得一些關於這些複雜問題的深入見解,並且對科技的未來發展有更清晰的認識。
评分「拯救或毀滅世界的十種新創科技」,這個標題實在是太霸氣了!它直接切中了我們這個時代最核心的議題之一:科技的雙面性。我一直在思考,在現今這個快速變遷的世界裡,究竟有哪些技術,是具有如此巨大的潛在影響力?是那些能夠徹底改變我們生活方式的AI應用,還是那些能夠重塑地球生態的環境科技?又或者是,那些能夠拓展人類生存邊界的太空探索技術?我非常期待書中能夠深入探討這些科技的原理、它們的發展趨勢,以及最重要的,它們可能帶來的長遠影響。尤其是,作者是如何評估這些科技「拯救」或「毀滅」世界的可能性?是基於嚴謹的科學分析,還是結合了哲學和倫理的思考?我希望能從這本書中,不僅僅獲得知識,更能獲得一些思考的啟發,讓我們在面對科技的洪流時,能夠做出更明智的選擇,確保科技的發展,最終能夠導向一個更美好、更可持續的未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