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尽在一池清水里、一张凳子上;
日本笑话始祖,
滑稽文学经典,
重现江户风俗、风趣。
《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两书是日本江户时代古典文学中「滑稽本」的代表作品,鲜明的描绘了平民百姓诸多身份、个性,以及生活样貌。
《浮世澡堂》共两编,前编是男澡堂,从清晨到午后,来的有瘫子豚七、七十岁的隐居老太爷、带着孩子的金兵卫、胡吹乱奏的江湖医生、错把别人内裤当毛巾的外乡人、醉汉、瞎子等人物;二编则描写女澡堂,有艺妓、使女、女儿、母亲、媳妇、婆婆、乳母等十六个景。《浮世理发馆》则捕捉前来理发的客人,或是无所事事晃来晃去的无聊汉等等,闲言女人、争相为猫取名,大谈失败、吃醋谬论,间或嗟叹世道⋯⋯
日本说笑艺术重要文化财前身,借着你来我往的对话应答,有世态,也有人情,谑而不虐,逗趣横生。
两书内容尽管多渉市井,但用字遣词因时代背景不易解读,长期让译者却步,截至目前,中国作家周作人译本,公推最为到位,尤其大量的註解更是集江户文化之大成,周作人自己也相当满意:「能够把三马的两种滑稽本译了出来,并且加了不少的註解,这是我所觉得十分高兴的事。」
本(两)书虽然年代已远,但其中显现的日本庶民文化,读者却不会陌生,尤其是日本人称钱汤的公共澡堂。而繁体字版更邀请研究日本风俗人文的蔡亦竹老师,和旅游专家工头坚,就文化和旅游两方面导读。
蔡亦竹:要理解日本式的幽默,其实对于日文的构造和风土民情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就是两本最好的参考书物。
工头坚:近年由于东京晴空塔在隅田川东岸之落成,带动了墨田区「下町文艺复兴」的风潮,如果能够搭配式亭三马的小说,则当时「江户仔」的生活,更是活灵活现。
除此之外,还有插画家洪福田仿浮世绘风的版画,模拟这两处江户庶民聚集所的生活样貌,惟妙惟肖。
*随书附赠精美插图拉页*
名人推荐
蔡亦竹(实践大学助理教授)、工头坚(《旅饭》创办人、《时代的风》作者) 导读、推荐
著者信息
式亭三马
日本小说家。 生于江户(今东京 )。 当过书店学徒,卖过药品、化妆品和旧书。 经商之余从事创作。 1794年发表《天道浮世出星操》等作品。 他主张继承小说传统,19世纪初开始创作滑稽小说,代表作有《浮世澡堂》、《 浮世理发馆 》以及《四十八种怪癖》、《古今百愚》等,据传有135部,为世人所注意。 他强调写实,反对在作品中说理和空谈,也不搜胜猎奇,而往往通过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和普通小人物的描写,反映世态炎凉,揭露人性的弱点,如现代所谓的黑色幽默。 他笔下的人物个性鲜明,心理描写逼真,语言富于特色,被认为是日本古典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1822年殁,享年48岁。
译者简介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
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着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
图书目录
初编卷上
柳发新话自序
理发馆所在
隐居与豪杰
腐儒孔粪的气焰
隐居与传法论《大学》
麻脸的熊公
婀娜文字
卖点心的
初编卷中
德太郎与伙伴
评论女人
上方的商人作兵卫
作兵卫的失败谈
长六的猫
中右卫门找儿子
初编卷下
淘气的徒弟
食客飞助
钱右卫门
泷姑的乳母
后序
二编卷上
序
巫婆关亡
谈论吃醋
婆关亡之二
女人的笑话
钱右卫门谈失败
二编卷下
马阴的失败
阿袖的成名
理发馆的内情
占波八卖鸭子
流行俗歌
读《三国志》
豁拳赌吃面
女客阿袋
图书序言
日本笑话本 浮世人间像
日文里的「笑い」,其实是种高度文化。
笑其实是人类的本能,不管任何种族或是文化下成长的人们,都可以经由「笑」这种最原始的脸部表情,表达自己的愉悦和善意。虽然也有学说指出「笑」的露齿表情是从原始人类的威吓动作演化出来的,但对现在的文明人来说,笑容代表的就是开心和喜悦,还有感情的共有。
虽然笑是本能,但是引人莞尔的笑料和笑点可就随着国家和地域不同而大相径庭了。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看日本综艺节目里观众和来宾笑成一团,但是自己在电视前却从头到尾搞不清楚笑点在哪的经验。因为让人发笑需要技术、需要幽默感,而幽默感又必须建立在双方具有共同文化累积的前提上。就像日本笑匠三巨头的田毛利(タモリ)、明石家秋刀鱼、北野武在台湾知名度不高,是的,你或许知道北野武是有名的导演,就像欧美所认识的「世界 のKITANO」一样,但是他的本职是搞笑艺人,至今仍常常穿着各种奇怪的布偶装出来主持节目。而他本人也自认「ビートたけし」(北野武作为搞笑艺人的艺名),才是他真正的「身分」。但是北野武作为搞笑艺人的元素,却没有像他作为导演的艺术元素般广为台湾人所知。同样在日本极负盛名的志村健在台湾却是几乎家喻户晓。原因就在于志村式的搞笑常诉诸于直觉的狗吃屎、大脸盆或是怪叔叔甚至下流梗,而上述三位的幽默则是需要对日本文化有一定认识,田毛利主打的是大叔风格的成年白烂风,明石家擅长关西流的话术,而北野武则是典型东京「下町」庶民式的搞笑。
综合以上,要理解日本式的幽默,其实对于日文的构造和风土民情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否则我们就真的只能停留在欣赏纯白烂的胡搞瞎搞──虽然这些我们看来是胡搞瞎搞的大爆笑桥段,在日本其实也是经过精心设计和构筑的艺术成果。我们当然不可能为了要看懂日本的搞笑节目就去精通日文,但是我们却可以经由对日本许多资料,甚至古典的欣赏去接近日本的幽默之心。《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就是两本最好的参考书物。
从发祥自一千多年前平安时代的传统艺能「狂言」起,日本的表演艺术中就一直有着「搞笑」这种元素存在。尤其是到了「三百年太平」的江户时代,这种搞笑的血脉在表演艺术中被歌舞伎、人形净琉璃等艺能继承,更以「落语」这种类似单口相声的高等说唱艺术的形式集其大成。而落语和另一种形态相近的传统艺能「漫才」更是孕育出许多现代搞笑艺人的摇篮,前面提到的笑匠三巨头里,明石家秋刀鱼就是命名自入门学习落语时代的师父,而北野武虽然出身漫才界,却也在成名之后还以「立川梅春」这个落语家的身分公开演出过落语曲目。而搞笑精神发挥在文学上,就是以《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代表的所谓「滑稽本」了。
当然,幽默感是会随时代改变的。就算同为台湾人,我们现在去看四十年代的台湾喜剧电影,也说不定看不出笑点在哪里。因为生活形态随着改变,就像五十年后的人们可能无法理解,我们看到路上有人一边骑车一边用智慧型手机传LINE,然后在十字路口和另一个三宝相撞飞出去还掉到资源回收车上有多么好笑。那么我们也不是日本人,又何必特别去看江户时代写成的滑稽本?理由很简单,因为作为文字流传下来的滑稽本,和作为表演艺术相传至今的落语,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滑稽本中的对白会使用如落语家般的幽默生动对话,而落语也常从滑稽本里的有趣故事取材作为表演剧目。落语其实分为「创作落语」和「古典落语」,创作落语当然就是由落语家自由发挥才能编写好笑的故事,但是古典落语则是有固定的脚本内容和题材。也就是说观众其实早就知道故事的结果,就看表演者的技术和人格特质来决定是否能让已经听了同样故事好几次的观众们哈哈大笑了。这种存活于现代社会的传统艺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观赏一部十多年前由长濑智也和冈田准一主演的日剧《虎与龙》去更深入地了解。而古典落语的精髓,就是《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里的「熊公」、「隐居」、「土龙」等,有时犯蠢、但有时又充满世间智慧和哲理的市井人物百态,这就是所谓的「浮世」美学。
总之,滑稽本就是现代日本搞笑哲学的始祖。而以浮世绘广为人知的「浮世」概念,更是江户时代太平盛世培养出来的平民哲学。江户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在这个大都市里生活的庶民们,一边过着因身分制度而受限于自己出生背景、却不必担心因战乱而流离的安定生活,一边又因为日本的四季风情和佛教思想培养出来的无常观,而发展出了称为「粋」的美学。所谓的「粋」就是通晓人情世事并且洞察感情之精微,不管是思考或是言行都必须洗练而且带有美感的哲学。这种听起来似乎难以理解和实践的精神,其实就是江户庶民们的理想人生境界,勉强翻成华语就是「会心一笑」和「帅气」的结合体。如果说得更白话,其实就是《深夜食堂》里客人们与老板间的互动交流。在木造房屋占建筑物绝大比例,而把火灾视为最恐怖灾害的江户,一般人是不允许在家中生火烧洗澡水的,所以只要是平民百姓,大家都得在澡堂袒裎相见。这种庶民生活中的必需行为,意外地与茶道一样形成了「众生平等」的美学,而理发馆则是当时人们聚集打屁之地。如果现代人为了和人交流和排解空虚而在深夜食堂集合,那么江户时代的人们则是在澡堂和理发馆里看到庶民们的人生百态。
由式亭三马这位庶民作家所写、并由鲁迅之弟周作人翻译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就是上述精神的文学结晶。江户时代虽然因为身分固定的关系而缺乏社会阶层流动,但近三百年的和平却也带给日本史上少见的高生活水准。大都市江户的庶民们除了忙于生活之外,印刷业的发达和惊人的平民识字率,也让滑稽本这种当时或许不登大雅之堂的平民读物得以流行,还在后世成为了了解日本平民文化和幽默传统,甚至是日文演进的宝贵资料。所以对于日本文化有兴趣的您,绝不可错过这两部记载了数百年前日本人喜怒哀乐的搞笑始祖经典。
蔡亦竹
(专攻日本民俗学,实践大学应用日文系助理教授)
推荐序
浮世江户的时光旅行
有些人梦想中的旅行,是前往遥远的天涯海角;又有些人的梦想旅行,则是前往某一个特定时空。拜交通发达之便,天涯海角容易抵达,反倒是已逝去的时代或风景,则是几乎不可能「到达」了。
作为一个旅行者,常在各地的城市中行走,对于城市的空间环境,虽不敢说具备什么太专业的眼光或观点,但浮光掠影般的感受总还是有的。欧洲不少历史名城,行走在巷弄之间,彷彿走进数百年不变的场景,那种时空重叠的错觉,拓展了旅行这件事本身的空间侷限性,而与个人的阅读和感受交融在一起,获得了更多愉悦与惊喜。
曾有两次机会与被誉为「东京学的第一人」的日本当代作家、文艺评论家川本三郎先生同桌共宴,作为对于东京这座城市富有感情与兴趣的后辈小生,鼓起勇气提问:「东京学」的定义究竟为何?结果先生的答案是,由于以「东京」为名的城市历史仍嫌太短,如果真要话说从头,则必须称为「江户东京学」才算完整。
今日走在东京街头,看到的是高楼林立、巷弄密集的水泥丛林;但若说到江户的历史,很多日本战国史迷,对于这一段应该都很熟悉了:德川家康被猴子关白「移封(贬)」到距离京都遥远的江户,励精图治、韬光养晦,最终西进击败丰臣势力,一统天下,此举也令关东(江户)逐渐取代关西(京都、大坂),成为日本的政经中心。
但其实家康初到江户,那是一片水乡泽国的鸟地方。因为当时利根川和荒川等河流纵横,遇雨氾滥,江户城周边基本是湿地。德川家前后花了一甲子,历经数代,进行「利根川东迁事业」,打通上游,将川流引向东,至铫子注入太平洋。此举把江户由湿地化为硬土,更灌溉了房总半岛的万亩良田,奠定关东兵强马壮、安居乐业的基础。
东京的地形西高东低,然而现今建筑密集,即使打开卫星地图,也未必能看得出其中奥妙,但如果上网找到日本国土地理院制作的数位标高地形图,便一目了然:在江户城(也就是现在的皇居)以西,基本就是武藏野台地的一部分,如果要细分,还可分为饭仓、三田、赤坂、青山、麻布、高轮、白金台地⋯⋯等小区域名称,这也就是所谓的「山手」(山的方向)。
旅客熟悉的山手线,现今已是环绕东京中心部的环状线,但十九世纪末兴建的时候,初期仅是从北端的赤羽到南端的品川,由于途经的区域都集中在当时人口较稀少的台地,便以山手线得名。作为旅人搭乘山手线那么多年,心想整个环形区域不可能全都是「山手」啊,直到查询初期历史来看,才得以解心中之惑。
而既有「山手」,便有与其相对的「下町」,同样地如果从标高地形图来看,就会恍然大悟,当时的江户城,盖在台地边缘,居高临下,威风凛凛;而其以东的区域,毫无疑问便是将军脚边的「城下町」了。尽管过去数百年,陆续化湿地为陆地、甚至填海造陆,东京的海岸线与江户时代相较,已有极大的不同,但老城下町的范围,看来基本还是集中在神田川畔、地势稍微不太低洼的区域,从神田、马喰町、浅草,再跨过隅田川,也就是现在的台东和墨田这两个区。
说起来不无可惜,由于东京在过去百年间,陆续受到地震与轰炸的灾难洗礼,几乎可说是一座在战后重建的城市,想要寻访江户时代的街道风情,正如本文开头的感叹,多已随光阴逝去。有一种方式是远离城区,前往邻县以「小江户」闻名的川越或佐原;或前往位于东京都西边小金井市的江户东京建筑园,但那说到底毕竟是主题乐园式的复原或仿造,而非原地原味的生活场景。但如果想在「现地」寻访昔日风情,似乎只能前往位于两国的江户东京博物馆,透过馆内的展示以及体验活动,一窥当年江户下町庶民的生活面貌。
理解地形的高低起伏,看过了博物馆的动静态展示,固然能对当年江户的面貌有更清楚的概念,心中有了场景,然而在这场景中生活的人们,他们的日常、穿着、对话,仍无法凭空想像。于是只好从艺术作品当中去找寻。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浮世绘师,以他们的才华与观察,留下了一幅幅反映当时江户庶民生活面貌的精美作品,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无疑是葛饰北斋。江户东京博物馆中的展示,也可看出不少由浮世绘中撷取的元素去复原。
所谓「浮世」,根据我查到的日文解释,有「现代风」、「当世」的意思,但又带点「好色」的意涵。或者应该说,原本「浮」这个字,有「浮气」的用法,便是轻浮好色偷腥的代名词;又如台湾的外来组合语中,便有损人「浮浪贡」的称唿(亦即现在一般说的噗拢共),亦是形容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之人。虽然听起来似乎都不是什么正面的评语,但却不得不承认,这「浮世」的生活风格,又岂不是人们(或至少是我)心向往之、却不敢为的处世态度?而那个浮浪的时代已然逝去,更增添几番心下之憧憬。
近年由于东京晴空塔(Tokyo Sky Tree)在隅田川东岸之落成,带动了墨田区「下町文艺复兴」的风潮,更在两国近邻、开设了墨田北斋美术馆,而关于北斋以及其女儿、也是浮世绘师的阿荣之故事,也陆续被改编为小说、动画、电视影集,让这些原本寄託于二次元想像的情怀,有了更加立体与现代感的呈现;如果能够搭配与北斋同一时代的作家──式亭三马的小说,则当时「江户仔」的生活,更是活灵活现。至此,我心中寻寻觅觅的「江户场景」,才终于真正得以完整。
下次到东京,别只沉醉于「山手」的五光十色与购物时尚,也来探望「下町」的老时光与人文风韵吧。
工头坚
《旅饭》创办人、《时代的风》作者
图书试读
正说着话,鬓五郎留吉两人从里边出来。
鬓五郎:「劳大家久候了。」
德太郎:「特别快的早饭呀。——那个那个,看外边,外边。」用手指指着,大家都看外边。
圣吉:「哈哈,很清清楚楚的浮现出来了。」
贤藏:「是个美女呀。」
圣吉:「不是万叶家吧。」
贤藏:「是馒头家。」
德太郎:「好讨厌。」
圣吉:「哈哈,紫湖绉的衣裳,带子是八端织。」
贤藏:「衣裳看得很是清楚,我是只看那脸,所以此外都不看见。」
圣吉:「这里稍微有点不同。头上大略总计值三十两,梳子是散斑的玳瑁,搔头是时样的两支,后边的簪稍微样式过时,可是也是玳瑁的。」
贤藏:「眼睛两只,完全无缺,鼻梁笔直,通到爪尖。」
圣吉:「嘴巴裂开,直到耳边,牙齿是一列乱桩子。」
贤藏:「父母的报应在子女的身上。」
圣吉:「去你的吧。说些什么呀。」
德太郎:「但是倒是个美女。」
圣吉:「似乎是很风流的样子。」
贤藏:「大概有丈夫吧?」
圣吉:「那个老婆子在后边跟着,笑嘻嘻的走,那是她亲生的女儿。」
德太郎:「对,对。一点不错。」
圣吉:「若是媳妇,那就应该退后,让婆婆先走了。」
贤藏:「那里,那里,又来了。哈哈,这回来的是宅门子里的人。」
德太郎:「穿的是红里子的全身花样,结束整齐的,又是好哩。」
贤藏:「怎么样,这一个和刚才那一个,挑选起来是哪一个好呢?」
圣吉:「那么,挑选起来第一当选的是先头那个女人。但是假如要讨老婆,还是这一个安详得好。首先于家庭有好处呀。」
贤藏:「先头那一个是,一定吃醋吃得很厉害吧。」
德太郎:「虽然吃醋厉害,可是也很有手段吧。」
圣吉:「无论怎么样,老婆还是不风流、丑陋一点的好。这样说了,并不是我自己娶了丑妇,所以说不服输的话,那样的人也不懂吃醋的方法,无论说怎样的诳话,也相信是真实的,这其间可以在外边另找好的玩耍。」
德太郎:「第一是家里安静的好。」
贤藏:「你自己的老婆原是丑陋的好,不风流,安详温顺,很看重丈夫,讲俭省,家里安静,这是很好的。但是朋友的老婆却是俏皮,娇媚,者字号出身或是艺妓出身,酒也能喝,三弦也会弹,哎呀,你是什么呀,好漂亮的样子,特别会说笑,是这么的轻浮的人才好。」
德太郎:「这是谁都一样呀。」
用户评价
这本书我找了好久,终于在一家小书店的角落里发现了它。封面设计很有年代感,淡淡的复古色调,配上一个写意的水墨画,一下子就把人拉进了那个似乎不太真实又充满生活气息的世界。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纸张的触感也很好,翻开书页,字迹清晰,排版舒适,光是这一点就让人心生欢喜。我迫不及待地开始阅读,第一个故事就让我惊艳。作者的笔触非常细腻,仿佛用放大镜审视着每一个细节,从人物微小的表情变化,到环境光影的流动,都描绘得绘声绘色。我常常会因为书中某个场景的生动描写而停下来,在脑海里反复回味,甚至会想象自己就身处其中,感受着那份独特的氛围。
评分这本《浮世理发馆》真的是一本让人读了就停不下来的书。我尤其喜欢作者对人物心理的刻画,那种不动声色的忧伤,那种藏在笑容背后的失落,都写得入木三分。读着读着,你会发现自己好像认识了这些书里的人物,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挣扎与选择,都那么真实,那么有共鸣。有时候,我会觉得书中某个角色的经历就像我曾经经历过的一样,那种感觉很奇妙。而且,作者的叙事节奏把握得非常好,张弛有度,时而温柔细腻,时而又充满力量,总能恰到好处地抓住读者的心。每次读完一个章节,都会让我对接下来的故事充满期待,想要知道他们最终的走向。
评分我一直觉得,一本好书应该能在读完后,还在你的脑海里萦绕很久,甚至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浮世理发馆》绝对属于这一类。它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多面性,看到了那些平凡日子里隐藏的诗意与哲思。书中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片段,在作者的笔下却闪烁着动人的光芒,让人重新审视身边的点滴。我特别欣赏作者的文字,它不像那种华丽的辞藻堆砌,而是朴实却富有感染力,字里行间流淌着一种智慧和温度。每次翻开它,都感觉像是在与一位老朋友聊天,听他娓娓道来那些关于人生、关于情感的故事,每次都会收获一些新的感悟。
评分说实话,我之前对这类题材的书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浮世理发馆》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它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也没有跌宕起伏的冲突,但就是这样一种平静的叙述,却有着无穷的魅力。作者似乎有一种魔力,能够将最普通的生活场景描绘得引人入胜,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沉浸其中。我喜欢书中人物之间的互动,那种含蓄的关心,那种默契的理解,都充满了人情味。它让我明白,生活的美,往往就藏在这些不经意间,藏在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细节里。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醒我们,用心去感受生活,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平凡之下的不凡。
评分拿到《浮世理发馆》的时候,我正处于一个有些迷茫的时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但读着读着,这本书就像一盏温暖的灯,照亮了我内心的某个角落。作者的文字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它没有给予我明确的答案,但它让我学会了如何去面对自己的迷茫,如何去理解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书中那些角色的经历,他们的成长和蜕变,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开始更愿意去观察生活,去思考自己内心的声音。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像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与自我的对话。我非常感谢它,让我在这浮躁的世界里,找到了一份内心的平静。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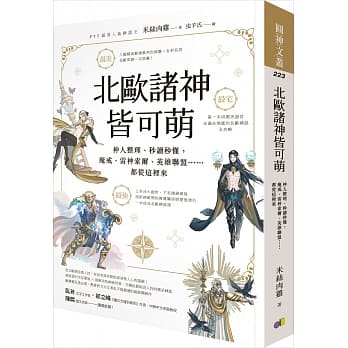
![北欧诸神皆可萌:神人整理、秒读秒懂,魔戒、雷神索尔、英雄联盟……都从这里来[限量签名书]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tbooks.qciss.net/0010765564/main.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