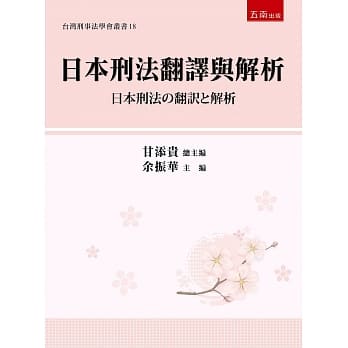具体描述
本书主要分为两部分,其一在于对少年事件处理法的学理有基础认知,其二是介绍目前少年事件实务处理流程,透过学理与实务的结合,除可供大学学生作为教材,对于将来有志从事司法人员更是不可或缺的书籍。
与一般传统教科书很大的不同是,本教材主要以因应公职考试之观护人考试编制,目前可报考观护人考试之科系有多数,例如犯罪防治、法律、财经法律、社会工作、心理学系等数科系,广泛使用之可行性高。由于目前之少年事件处理教材中多为传统法学用书方式呈现,本教材尚辅助当前实务工作资料编制,为国内首创此种学术与实务结合之教材创新。
著者信息
陈慈幸
现 职
国立中正大学犯罪防治学系暨研究所教授兼副主任
法务部司法官学院讲座
学 历
日本中央大学法律学博士
蔡孟凌
现 职
网路通路经营辅导
经 历
研究助理、资讯产业法务相关人员
学 历
国立中正大学犯罪防治研究所
图书目录
推荐序 李进雄
三版序
自 序
单元1 少年事件处理法之架构与法规
第一章 什么叫做少年事件?/3
第二章 少年事件处理法的特征与修法经过/13
第三章 少年事件处理程序图览/29
单元2 少年及家事法院:少年法院
第一章 少年及家事法院、少年及家事法庭/47
第二章 调查保护处的功能与调查保护官(观护人)的作用/67
单元3 少年保护事件概说
第一章 保护事件实际案例演习/81
第二章 保护处分与刑事处分之差别与实务演习/91
单元4 调查报告的撰写
第一章 少年事件审前调查/119
第二章 调查报告的格式与撰写/133
单元5 少年保护事件之调查及审理
第一章 出庭陈述与协商式审理/147
第二章 急速辅导、留置观察与交付观察/153
第三章 转介辅导/160
单元6 少年保护处分之执行──训诫、假日生活辅导
第一章 训诫与假日生活辅导之学理介绍/169
第二章 训诫与假日生活辅导实务案例分析/177
单元7 少年保护处分之执行──保护管束及劳动服务
第一章 保护管束及劳动服务之学理介绍/189
第二章 保护管束之实务运作/206
单元8 少年保护处分之执行──安置辅导与感化教育
图书序言
时光更是匆匆,本书又即将三版,事实上三版的预定已早在二年前,随着这本书的第一版至今已是八年,我跟孟凌一个在学界、一个在业界继续努力,再度感谢孟凌回头重新拾起笔,陪伴我对于第三版的期待。
这几年因研究走过不少国家,也度过许多生命的苦难,几年前一次德国的移地研究,让我思考了生命,也思考了少年事件处理法的学理与未来。
我所投宿的旅馆前,就是历史博物馆,如果用仰望的心看这栋建筑,那还真有些美感。每天中午,当研究完成一段时候,我会坐在这里思考一下子,这里是一个值得常坐与停伫的地方。
週末的市集,似乎是这里有趣的动词,一早,邻近乡镇的农家纷纷进到这里,我一向喜欢与熟悉这种有机市集,虽然我除了谢谢外其他德语也不会说,当我指着樱桃,讲出一公斤,农家就很高兴地秤出一公斤满满又硕大的樱桃给我了,交易的过程很简单,但微笑总是人与人之间很棒的连结,紧接着他们问我从亚洲哪个都市来?我笑着跟他们说,如果是十七年前,就是东京。
这一大包的樱桃,吃了很多天,在我这个年代的小孩,樱桃应该是属于罐头红樱桃的代名词,也很多人被这样的认知给定格,当小时跟父亲出国,在国外吃到新鲜的樱桃很高兴跟同班同学分享时,大多数同学告诉我,我认知的紫色新鲜樱桃的,都是想像的,因为樱桃的真实就是大红色的罐头装的腌渍物。
当时年纪还非常小,一个人说不过全班五十几个小朋友,当极力解释都无法胜过那五十几张嘴时,一个片刻,选择了沉默,也选择了一点妥协,虽然我知道樱桃的真相。
随着知识与讯息的进步,对于樱桃,再也没有人认为是大红的腌渍物品时,但很可惜的是,很多人还是被自己的主观认知给定格,于是我一直在想,当年那些对着我说樱桃是大红腌渍品的同学们,他们的思绪是否依旧还是在现今社会八卦新闻飞舞着,想到这里,就想起当时孤单地拿着樱桃照片大力诉说真相的小学低年级生的自己,然后还要屈服群众压力的小学低年级生的自己。
所以,我们要鼓励少年时,是否在某个时候,我们也被主观给定格了呢?
市集的广场很热闹,很有趣的是,这里的热闹带着一股寂静,北方国度给予人的一种简单的平静,来往的旅客不少,大家急着拍照,却很少像我一样驻足感受宁静。对于很多人来说,对于旅行的记忆,是留下一些实质的东西,拍照真是留下一种实质的深刻的好东西,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的我,轻轻地放下相机了。
闭上眼睛,听着微微的风声,那轻轻的声响,慢慢穿越过灵魂的深处,再浸淫到一些的记忆,过去一些苦闷的回忆,慢慢地升起,然后我思考着过往的一切,转折的痛苦与撕裂,让体感有些沉重,但周遭的宁静,却拥抱着这样的自己,
树叶的飘落,洒在身上,多了一些温柔,暖暖的阳光与冷冷的风,思维飘荡这么远的距离,终于有了意义。
这样的一个夏天,在森林拥抱着温柔,其他的研究员提醒着我要学几句简单德语,学了一些以后,常用的就是「谢谢」,似乎忘了学「再见」,事实上,我的离开是几天后的清晨,依旧温柔的风与树,洒满了一身的落叶,夏天,或许不应该有这么多的落叶,然后,真的在想,这是德国一种别致的道别。
风依然悠悠,早夏的德国天际好高,那个绝对的蓝,清澈无比,犹如少年的眼神。
2018年2月日本中央大学御茶ノ水记念馆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视角,审视台湾的少年司法体系。作者并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现有的制度,而是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例如,作者批评了台湾的少年感化制度过于封闭,缺乏与社会的联系,导致少年出狱后难以适应社会生活。作者建议,应该加强感化院与社会的合作,为少年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和就业机会。这种建议,我认为非常有价值。此外,作者还指出,台湾的少年司法体系过于强调惩罚,而忽略了预防和教化。作者建议,应该加大对少年犯罪预防的投入,并加强对少年犯罪者的心理辅导和教育。这本书的另一个亮点在于,它关注了弱势少年的权益。作者指出,来自贫困家庭、单亲家庭或遭受家庭暴力的少年,更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作者建议,应该为这些弱势少年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和帮助。这本书虽然有些观点比较尖锐,但它能够引发我们对少年司法问题的深入思考,这才是它最大的价值。
评分说实话,这本书读下来,我感觉有点压抑。它冷静地剖析了少年犯罪的残酷现实,也揭示了社会对少年犯罪者的偏见和歧视。作者用大量的篇幅,探讨了少年犯罪的社会成因,例如贫困、家庭暴力、教育不公等等。这些因素,的确是导致少年犯罪的重要原因,但仅仅强调这些因素,似乎也忽略了少年自身的责任。我并不是说要对少年犯罪者严惩不贷,而是认为,在强调社会责任的同时,也应该引导少年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本书的另一个不足之处在于,它缺乏对“修复式司法”的深入探讨。我认为,修复式司法是一种更具人道主义精神的处理方式,它强调的是让犯罪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主动修复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够将修复式司法引入台湾的少年司法体系,或许能够更好地促进少年犯罪者的回归和社会和谐。
评分这本书的结构安排相当清晰,从少年事件的定义、处理流程到配套的社会福利制度,都有涵盖到,这让我对台湾的少年司法体系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作者在讨论预防少年犯罪方面,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观点,例如加强家庭功能、改善学校环境、提供多元化的教育资源等。这些建议都强调了预防胜于惩罚的重要性,也体现了对少年权益的尊重。然而,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在讨论“教化”方面略显不足。虽然作者提到了感化院的作用,但并没有深入探讨感化院的实际运作情况,以及感化院的教化效果。我很好奇,感化院是如何针对不同类型的少年犯罪者,制定个性化的教化方案的?感化院的教化人员,是否接受过专业的心理辅导和危机处理培训?这些问题,如果能够得到更详细的解答,将会使这本书更加完整。另外,书中对于被害人权益的关注也稍显不足,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更加平衡地关注少年犯罪者和被害人的权益。
评分读完这本关于少年司法体系的书,感觉像是走了一趟迷宫,却始终找不到出口。作者试图用宏观的角度去探讨少年犯罪的成因、处理方式,以及社会对少年的期待,但行文过于理论化,缺乏实际案例的支撑,读起来相当吃力。尤其对于我们这些非法律专业人士来说,书中的许多专业术语和复杂的法律条文,简直是天书。我期待的是一本能将抽象的法律概念,转化成具体、生动的案例分析,让我能够理解这些法律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运作的。例如,书中提到“弹性空间”,但并没有详细解释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中,这个“弹性空间”具体如何运用,以及可能造成的争议。此外,书中的观点也略显保守,对于一些新兴的犯罪形式,例如网络犯罪、校园霸凌等,讨论不够深入。总而言之,这本书对于法律专业人士或许有参考价值,但对于想要了解少年司法体系的普通读者来说,恐怕难以入门。我希望未来的作品能够更加注重可读性和实用性,多一些案例,少一些空洞的理论。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非常平易近人,作者用生动的案例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复杂的法律概念解释得非常清楚。我尤其喜欢书中对于“少年审判”的描述,作者详细地介绍了少年审判的程序、原则和注意事项,让我对少年审判有了更直观的了解。例如,作者提到少年审判的“不公开原则”,并解释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少年的隐私,避免对少年造成二次伤害。这种解释,让我对台湾的少年司法体系更加信任。此外,书中还讨论了“假释”和“保护管束”等制度,并分析了这些制度的优缺点。这些分析,让我对少年犯罪者的出狱后管理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总而言之,这本书是一本非常适合普通读者阅读的入门书籍,它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台湾的少年司法体系,并引发我们对少年犯罪问题的思考。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