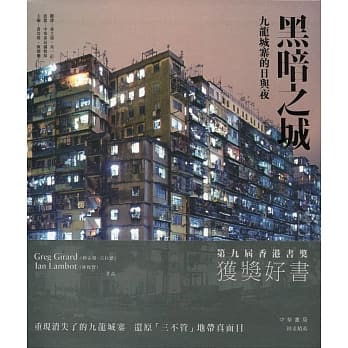具体描述
鲜明呈现极端的残暴,传递疼痛
本书借鉴对中日战争中战争罪犯的第一手採访,以夹叙夹议的方式,带领读者进入种种骇人听闻的罪行。但这本书所问的并不是战争罪犯这回事,而是企图去贴近他们,进一步思考暴行是如何被观看、如何被感受?促使暴行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如何才能停止暴行?然而,最终我们可能被迫承认,人类拥有难以回答的问题,并承认这些问题可能没有令人安慰的答案。
解开「邪恶」的真相――
邪恶,它长什么样子?它感觉起来是什么样子?它缘何产生?
邪恶的样貌既不横眉怒目,也非青面獠牙。
其特质不是大奸大恶,而是正常到可怕的「平庸」。
人们总是素朴而侥倖地以为,邪恶不会降临在自己身上。善良悲悯如我等,绝不可能成为恶;安分守己如我等,更不能成为恶的受害者。
但是万一,万一那天真的降临,除了悲愤控诉或同流合污,我们真的敢于抵抗邪恶所施加于的暴行吗?战时犯下「反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的战犯、相信强暴妇女是种族清洗必要手段的圣战士,以及被捕后露出诡异微笑的杀人兇手等,无一不是如同你我的平凡人,他们和我们一样努力生活、遵守交通规则、渴望得到幸福和成就感……为什么?为什么做得出「那种事」?
或许,邪恶的特质不是大奸大恶,而是正常到可怕的「平庸」。作者对二战日本老兵进行第一手访谈,以小说家的笔法抽绎他们的战时回忆,串起了本书各主题之间的脉络,但这些回忆只是一种人类情感的显影剂,借以还原「邪恶」的真相、成因、背景,及其内隐的意涵。
作者试图把所有关乎邪恶的讨论聚焦在那些我们不忍卒睹、刻意忽视的黑暗角落——放大、拉近,强迫观看,挑起了人们在面对历史上的战争、屠杀、暴力时的一连串偏见与错误想像,再从观者震惊、尴尬、不解等情绪中,将之一一拆解,加以釐清,赋予定义,并延伸至各个学术面向,进行开放性的严肃讨论。
本书的写作超出学院论述的边界之外,论述结构更有别于以往类似主题的出版品,採回文形式呈现,未分章节,一气呵成。正义不一定只站在哪一边,如此跨界而绵密的讨论,为的是处理「邪恶」这一巨大命题时能不偏重任何一个片面的武断。
讨论范围既广且深―—从鄂兰(Arendt)谈到津巴多(Zimbardo),从凶残谈到原谅,从道德制约谈到人性慾望,从「再现的弔诡」谈到战争的泪水,内容扩及哲学、伦理学、宗教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美学等范畴,同时也触及到人们在观看暴力、陈述暴力时可能遭遇的道德伦理风险,特别是在现今社会,你我都可能成为暴力行为的观者(或帮兇?),有些界线我们必须即刻釐清。
最后,作者提醒我们,当面对「邪恶」的拳头如雨落下,唯一能做的最好还击也许是「宽恕」。本书中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将会怎样影响我们的世界观、对人类未来的看法、最后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端看我们的「同理心」能发挥多大效用,此一困难的人性钻探,将在阅毕本书后得到解答。
名人推荐
道斯对暴力进行了深度和范围宽广的沈思。他从鄂兰(Arendt)谈到津巴多(Zimbardo),从凶残谈到原谅,从再现的吊诡(paradoxes of representation)谈到和战争的泪水(真诚或不真诚的泪水)。书中日本老兵所述说的故事让人不得安宁。道斯一方面以社会科学家眼力掌握凶残的成因,又以小说家的眼力抽绎出暴力对当事人的个人意义、自惠性和哲学蕴含。这是一种稀有的成就。转述刑求者自白的着作不下一百五十部,但从未有一部带有如此强烈的文学自觉。——贾礼(Darius Rejali),《刑求与民主》(Torture and Democracy)作者
这部非同一般的书让人惊恐、愤怒和困惑。道斯把我们带进犯了「反人类罪行」罪犯的思想世界,同时又提醒我们,没有若干互相信赖就不可能进入别人的心灵。《恶人:普通人为何会变成恶魔》与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格斗(即设法从它看见的事情理出意义),但更重要的是,道斯的凝视从不动摇。——费尔德曼(Noah R. Feldman),哈佛法学院
《恶人:普通人为何会变成恶魔》超出学院论述的边界之外,其结构很多方面都与别不同。道斯不但钻探了人可以有多凶残,还以原创和近乎不能复制的方式探索了我们对那些行为不能见容于文明社会的人可有多大的同情心或同理心。——哈帕姆(Geoffrey Harpham),国家人文学中心
著者信息
詹姆士.道斯 James Dawes
剑桥大学哲学硕士,哈佛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哈佛大学院士学会青年院士,美国英语文学教授,擅长领域包括:反文化;人权:文学与语言理论;暴力与创伤;文学与哲学。其着作《恶人:普通人如何变成恶魔》(Evil Men, 2013)获国际人权图书奖;《好让世界知道》(World May Know: Bearing Witness to Atrocity, 2007)入围独立出版图书奖决选名单。另着有《语言的战争》(The Language of War, 2002)。不时在各大媒体(全国公共广播电台、BBC、保加利亚国家电台、《波士顿全球报》、《高等教育纪事报》和CNN网站等)亮相或撰稿。
译者简介
梁永安
台湾大学文化人类学学士、哲学硕士,东海大学哲学博士班肄业。目前为专业翻译者,共完成约近百本译着,包括《文化与抵抗》(Culture and Resistance / Edward W. Said)、《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 / Peter Gay)、《现代主义》(Modernism:The Lure of Heresy / Peter Gay)等。
图书目录
《恶人》正文
参考书目
致谢
图书序言
本书要谈的是凶残:它长什么样子,它感觉起来是什么样子,它缘何产生,有什么方法或许可以防治。整件事情起于我和摄影师纳德尔(Adam Nadel)到日本採访一批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战犯。他们年老衰弱,很多年过八旬,年轻时曾干过最让人发指的恶行。他们最终全被俘虏,在战犯营里关了十年。他们给我看战争岁月的照片︰褪色黑白照里那个年轻人穿着军服,表情或自豪或害怕,或兇狠或稚嫩。看着自己的年轻自我,他们说他们看见的是虚空,是恶魔。
我参与人权工作多年,但之前从未访谈过加害者。事前我完全没料到这些访谈会让我晕头转向,更让我吓一大跳的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自己竟开始以受访者的眼睛看世界。本书的风格和结构都是为分享这种奇特经验而设计。本书不只是关于战争罪犯干过些什么,还是关于跟他们就近相处是什么感觉。
以下,我会把本书要探问的问题归结为五大群组,而它们也构成本书的一幅概念地图。本书的推进方式是模仿一个变焦镜头的移动:先是用广角镜把整个画面收入,然后用近镜慢慢推进以显示细部——这时细节虽已被扩大的焦点隐没却仍然鲜明,就像是凝视太阳太久在视网膜留下的印象。然后镜头会转至另一个关怀重心。
在逐一处理以下五大群组的问题时,我将会突出它们内含的一些弔诡。诗人济慈(John Keats)在一个不同脉络提出过所谓的「守虚能耐」(negative capability):那是一种在面对不确定、神祕和疑惑时仍能保持敞开的能力,拒绝把一切化约为熟悉的语汇和范畴而使之可为我们所控制。「守虚能耐」——还有它在文体领域的堂兄弟「错置」(juxtaposition)——让我们可以把弔诡经验视为一些开放性问题,有时还可以让我们在语言表达穷歇无灵之处经验到意义。
1.书写或阅读一本这样的书存在哪些道德风险?在观看暴力和创伤性事件时,我们要如何方能怀抱尊重和关怀而不致流于看八卦的好奇心态?深邃的私人创伤要如何方能呈现于公共空间?这些问题的答案中心皆包含一个起到结构作用的弔诡︰创伤的弔诡。我们既有道德责任去再现(represent)创伤,亦有道德责任不这么做。
2.如果我们打算一同经历这些骇人听闻的故事,它们对我们有何用途?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回答以下这类问题吗:社会是怎样把普通人变成恶魔?当事人会经历什么样的心理过程?有鑑于这些恶魔往往是男人,性别在种族清洗上扮演着什么角色?再一次,这些问题的答案皆是环绕着一些关键性弔诡旋转,包括了「邪恶的弔诡」(「邪恶」既是妖魔和他者,却又是平庸和人人皆干得出来)和「责任的弔诡」(我们是自由和自我决定,同时又是环境的产物)。
3.把镜头拉回︰这些骇人听闻的故事会怎样影响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对人类未来的看法、我们最后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我们对利他主义、超在(transcendence)甚至是「神」(the divine)的观点?牵涉其中的是一些我们熟悉的弔诡,包括「利他主义的弔诡」(利他主义既要求我们为利益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但我们利益他人时又往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虚无主义的弔诡」(我们必须面对自己的无意义性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意义),以及基督教版本的「恶的弔诡」(全能和全善的上帝如何能容许罪恶疾苦的存在?)
4.经历过会震撼我们良知和动摇我们世界观的暴戾残忍之后,宽恕是可能的吗?个人或国家在犯下滔天大罪之后还能指望获得饶恕吗?既然历史本身就充满谎言,而人的记忆力又总是不牢靠、自我保护和自利,你如何指望加害者能忠实自白?事实上,真相在战争、刑求和自白中有其位置吗?有的话又是什么位置?思考这一系列彼此相关的问题会驱使我们不断回到「自白的弔诡」:自白(confession)既是疗癒所寄的文化形式,又是具有潜在破坏力的形式。
5.最后是最首要的问题。自白都是一些故事,有其自成一格的伦理(ethics)。然则什么又是更一般性的说故事伦理(ethics of storytelling)?对我来说,这里牵涉的正是最难以排解的弔诡:书写的弔诡。要书写别人的隐私生活,你必须培养出对别人的尊重和亲密关系;然而,要书写别人的隐私生活,你又必须把他们非个人化,予以建构、摆布和展示。很多人会从事书写或阅读创伤故事这种艰难工作,是因为相信此举可以提升人类尊严。说故事不只是人权维护(human rights advocacy)的最基本工作,并且是人类同理心的最基本工作。但我们说出的故事真的可以改变什么吗?如果可以,带来的又是哪一类改变?阅读暴力性和创伤性事件时,我们真的可以怀抱尊重与关怀而不是看八卦的好奇心态吗?当各位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将会发生些什么?
图书试读
啊,会,我怀念他们。你知道,他们大部分人都像兄弟。真的。他们真的就像是你的家人。
我可以想像……
对,我们一起出生入死。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比亲兄弟还多。对,我怀念他们。当然怀念。
*
每一次,我都会送给受访者一小包明尼苏达州的野生稻米。每一次,我一开始都会表现得笨嘴拙舌,反覆半鞠躬道歉,为同一件事情自嘲︰我连「很高兴跟你会面」乃至「谢谢」之类的简单日语都说不好。他们听了会面露微笑(我敢说他们会为此惊讶)。在在看来,我每次一开始就先自暴其短是件好事。
每天早上,我和摄影师会到饭店外面喝咖啡和吃酥饼。每天傍晚,女译员会带我们去找消遣:看歌舞伎,看武术表演,吃最好吃而不昂贵的寿司,去她最喜欢的老酒馆喝两杯。我们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唯独不谈那些我们採访过的老兵。
*
为什么我会干得出那样的事?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我本来只是个农家子弟,一个在农民家庭长大的人。这是我后来会思索的问题。对,你最终一定会觉得奇怪。唉,我不是个会干出那种事的人。
*
直至今晚以前,我不算是看过真正的格斗。日本有些武术表演很文雅,像是液体舞(liquid dances),但今晚的表演却是货真价实的打斗。其中一方眼见就要胜出。他把另一个男人压倒在草蓆上,用拳头狠狠揍对方的头,一次又一次。观众会随着每一下拳头闷声发出集体呻吟。挨揍的那个男人想必痛得厉害,但脸上却看不见任何表情。揍他的那个男人反而表情丰富,像是愤怒或害怕——但我说不出来是愤怒还是害怕。
因为忙着跟摄影师和女译员交谈,我过了很久才离场,并因此跟先前两位格斗者在电梯里凑巧遇上。这时我才看出来,他们其实不算是男人,只算是大孩子。我讶异于我的身高比他们高。但更让我震撼的是看见他们站在一起,有说有笑。从这个近距离,我可以看见败方的脸上破了皮︰想必是被草蓆擦伤。基于什么理由,我对他生起悲悯之心。我很想凑近问他:经历过方才的激烈打斗,你是怎样回到正常生活的?
用户评价
《恶人:普通人为何会变成恶魔?》这个书名,光是听着就足够让人脊背发凉,同时也充满了探究的欲望。我一直在思考,这本书是否会涉及到一些关于群体盲从、集体狂热,或者权威服从的研究?毕竟,历史上有太多例子表明,当个体融入一个群体,或者面对强大的权威时,个人的道德判断往往会被削弱。我非常好奇,书中是否会引用经典的社会心理学实验,或者结合现代社会中的一些网络暴力、群体欺凌现象来论证?它是否会揭示,在 anonymity(匿名性)和 deindividuation(去个体化)的影响下,普通人是如何变得肆无忌惮,甚至做出令人发指的行为的?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科学的解释,让我们理解那些看起来“正常”的人,是如何在特定的环境下,蜕变成“恶魔”的。这本书的价值,我认为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人性的脆弱以及社会环境的巨大影响力。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简直抓人眼球,《恶人:普通人为何会变成恶魔?》。我当初就是被这个标题吸引住的,总觉得这里面藏着什么惊人的秘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也很有意思,不是那种浮夸的血腥或者阴森,反而透着一股冷静的、近乎哲学的光泽,让人忍不住想要翻开。我一直对人性的黑暗面感到好奇,总是在想,那些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情的人,他们真的是天生如此吗?还是有什么我们看不到的催化剂,一点点将他们推向深渊?这本书似乎就是试图解答这个古老而又令人不安的疑问。它挑战了我们对“恶”的固有认知,不再简单地将其归咎于少数“天生坏种”,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乃至个体心理的复杂交织。我尤其期待书中对“普通人”这个概念的探讨,毕竟,我们每个人都自认为是个普通人,但谁又能保证自己永远不会跨越那条界线呢?这本书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可能存在的阴影,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以及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希望它能提供一些令人警醒的视角,而不是简单地满足窥探欲。
评分从这本书的名字《恶人:普通人为何会变成恶魔?》就能预感到,它绝非一本轻松读物,而是一次深入人心的探索。我对于书中能否提供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案例或者理论分析非常感兴趣。我猜想,作者可能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心理学、社会学甚至哲学理论,来支撑他的观点。我期待书中能够展现出一些具体的、令人信服的论据,比如对历史事件的重塑解读,或者对现代社会一些普遍现象的深刻揭示。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我理解,那些看似不可思议的恶行,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其中的心理机制是怎样的?它会讲述那些“恶魔”们在蜕变过程中的挣扎、麻木,还是他们对自身行为的合理化?这些都是我非常好奇的。我希望这本书不仅仅停留在“为什么”,更能提供一些关于“如何避免”的思考。它能否成为一本警示录,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警惕,识别那些可能诱发“恶”的苗头?这本书的深度和广度,是我对它最大的期待。
评分这本《恶人:普通人为何会变成恶魔?》给我最深的感受,是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读视角,让我对“恶”的理解不再是单一的、非黑即白的。它似乎不满足于将恶行简单归结为个人道德败坏,而是深入剖析了社会结构、权力运作、群体心理乃至于日常环境如何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在进行一场心理侦探,作者抽丝剥茧,将那些看似偶然的恶行背后隐藏的必然联系一一呈现。我特别留意书中关于“情境”的论述,总觉得很多时候,一个人是否会成为“恶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处的特定情境,而不仅仅是他自身的性格缺陷。这种观点既令人不安,又充满了力量,因为它暗示着,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改变某些外部条件,来预防“恶”的滋生。而且,书中对“普通人”的定义也相当值得玩味,它让我们意识到,恶魔并非远在天边,而是可能就隐藏在我们身边,甚至是我们自己身上。这迫使我们去反思,在哪些情况下,我们自己的行为也可能变得“恶劣”。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思考方式,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批判和指责。
评分这本书《恶人:普通人为何会变成恶魔?》的标题就仿佛在抛出一个巨大的谜团,让我跃跃欲试地想要去解开它。我一直觉得,“恶”这个概念太过模糊,总是被赋予太多道德上的评判,而这本书似乎想要将它剥离出来,用更理性、更客观的眼光去审视。我期待书中能够颠覆一些我们固有的认知,比如,它是否会告诉我们,有时候“善意”的缺失,或者“错误”的选择,也能导向“恶”的结果?它是否会探讨,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我们为了生存或者保护自己,是否也会做出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事情?我特别想知道,书中对“普通人”的定义,以及他们如何一步步走向“恶魔”,是否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论述。它可能不是一本直接教你如何做个好人,而是让你理解,人性的复杂性远超我们的想象。这种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我相信能带给我很多震撼。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