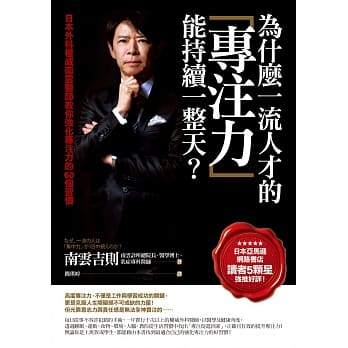具体描述
不整理书桌就无法工作、冲动刷卡购物好像不必付帐单、强迫性清扫、洗手、囤积、
找遍网站比价N次才下单……
这些行为真的不是你的错,因为,
强迫是一种慰借,让身体产生控制局面的幻觉,
有些还能帮助我们管理生活、让工作更有效率,
──有所成就的人,通常都有自己的仪式性动作,其实多半是强迫行为。
不过,厂商也会利用这点操纵你……想想《Candy Crush》、《愤怒鸟》是怎么让你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一直玩到手软。
作者雪伦‧贝格利曾任职于路透社、《华尔街日报》,是资深的科学专栏作家,
她指出,光是强迫行为的一种──强迫购买行为,美国就有高达16%的成人身陷其中,
其中有2%至4%的人有囤积症(同一种东西买到堆满家里,这可不是收藏家),
本书收录很多真实案例,探究四处可见的强迫行为,
原来,它没有我们想像得那么可怕,每个人多少都有,只是程度不同。
◎强迫不是成瘾,但多少与我们的行为有所关联。
上瘾是为了快乐,强迫行为是避免坏事发生!
赌博、酒瘾等成瘾行为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快感,强迫行为却是为了纾解心中焦虑,
例如,怕没收到新邮件,便不停检查手机。
‧后天的车祸意外,从此深陷强迫之中!
夏拉曾在车祸中受重伤,自此便出现强迫行为,驱使她进行不合理的仪式。
像是一定要把玩具、书本四个排成一组,不断的觉得自己的猫会跑进冰箱里。
◎这是我的仪式,怎么说是强迫 : 从投手上场前的小动作,到超尽责的同事。
.出于对美感与优雅的热爱——这是表达自我还是人格障碍?
遥控器一定要放在电视机上面、百叶窗的拉绳一定要卷起来,
他们会自订独特规则并严格遵循、重视纪律与责任,因为这是表达自我的方法。
你也有这种倾向吗?本书提供卡默测试,看看你对于规则的遵守有多疯狂
.上场打击前……与其他伟大人物的迷信
洋基球员米奇.曼托跑垒时一定会强迫性的碰一下二垒,
网球巨星纳达尔会用只有自己知道的仪式放水瓶,以特定的顺序拿毛巾,
他们说这是我的仪式,而仪式的本质就让人难以抗拒。
◎厂商也会利用这点操控你 : 电玩、手机和网路
‧不好玩还一直玩——电玩里的心理学陷阱
多巴胺会计算行动(例如,丢出愤怒鸟)带来报酬的机率,但大脑不知道这报酬
会有多好,便创造出紧张感,为了纾解它,玩家什么事都愿意做!
‧没有手机、没有网路,你会……?
网路强迫行为或许是企业花数百万美元所促成的!
某公司甚至有个职位叫做「强迫作用高阶产品经理」,企业还雇用顾问,
来发展网页浏览者的强迫体验,让你无法自拔!
还有非买不可、拾荒癖、顺手牵羊的强迫性获取,
不是利他、而是为自己的强迫性行善,
甚至,虔诚的信仰也常常是一种强迫行为表现……
原来每个人都有「不做,就很难过」的事情。
名人推荐
台湾临床心理学会理事长/姜忠信
两岸知名心理谘询师/邱永林
著者信息
雪伦‧贝格利(Sharon Begley)
STAT(《波士顿全球报》出版的生命科学刊物)的资深科学撰稿人。之前曾在路透社、《新闻週报》(Newsweek)、《每日野兽》(The Daily Beast)与《华尔街日报》任职。着有《脑部的情感生活》、《训练你的心智,改变你的脑部》、《心智与脑部》等书,也因为向大众传递科学知识而获得诸多奖项。
译者简介
廖桓伟
淡江大学经营决策系、东吴大学企管研究所毕业。
曾任网路电玩编译。现任出版社编辑,希望引进更多有趣(且畅销)的书,透过翻译来感动读者,译有《第三波数位革命》、《电竞产业的大未来》、《城市地底的城市》(皆为大是文化出版)。
图书目录
第一章 强迫作用源自焦虑,与成瘾不同
第二章 猫会不会在冰箱里?我这样算强迫症吗?
第三章 强迫行为该治疗吗?从雪地溅血到进军好莱坞
第四章 这不是强迫症,正好相反,是过份尽责
第五章 电玩的强迫行为——操纵你的多巴胺,操纵你
第六章 没有手机、没有网路,你会……
第七章 各种强迫行为的历史,是疯了还是古怪?
第八章 人都爱囤积,是定义自我、还是病了?
第九章 强迫性获取:非买不可、拾荒癖、顺手牵羊
第十章 强迫性行善,不是利他而是为自己
第十一章 强迫行为怎么造成的?大脑发生什么事?
致谢
图书序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迫行为,为了化解焦虑(节录)
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我把影响生活的强迫作用视为一种异状,而且它几乎到了令人害怕的地步:强迫自己反覆洗手的人;强迫自己打电动,打到大拇指抽筋的人;非血拚不可,导致循环信用到破产的人。但在我进行研究与报告的期间,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当我真正了解乍看之下像是疯掉的人,我发现他们的强迫行为并非完全没道理。相反的,他们的强迫作用,是因为担忧某些事物可能将他们生吞活剥,而产生的可理解反应。他们并不疯狂,甚至连崩溃都谈不上;他们在应对,让自己保持专注,而且比起让焦虑吞噬他们,这么做说不定还比较有用。
当我听了越多囤积癖(译註:过度收购或收集物件,即使是不值钱、有危险性或不卫生的物品)的动人故事,我发现自己思考的面向也越来越多。是啊,如果我也有一样的经历,那么我家也同样会塞满杂物,只为在自己与绝望的深渊之间,筑起一座堡垒。有强迫作用,并不代表脑袋崩溃。
我的第二个领悟是,虽然拥有极度强迫作用的人是异数,但驱使他们产生这些行为的焦虑,其实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主动平息焦虑的行为,是一种深沉且原始的冲动。这样的体悟,改变我看自己与周遭事物的角度:乍看之下轻率、自私、具有控制性或伤害性的行为,现在似乎都像是对恐惧与焦虑的可理解反应。
有轻微强迫作用的人,并没有达到精神病学上需要治疗的程度,但感到恐惧的形式与症状严重的人一样,强迫行为对他们的效果也相同。只是越深沉、越严重的焦虑,就需要越极端(经常是自残)的强迫行为来纾缓;而轻微的焦虑,只会让我们手机不离手、只根据自己了解的规格来洗衣服,以及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整理书桌。
把人变成这副德性的强迫作用,可说是千奇百怪,你能想像到的都有可能。
几年前,阿姆斯特丹一位65岁的老人,引起了心理卫生诊所的关切,因为16年来,他总是有股难以抗拒的强迫作用,想用口哨吹出嘉年华歌曲。「他老婆因为同一首歌听了快16年而几近绝望,只好向心理卫生诊所求助。」荷兰籍的精神科医师,在2012年发表于《BMC精神病学》(BMC Psychiatry)期刊的论文中写道:「他每天都要吹5~8小时,而且越累的话,吹得越难听。」
医师给「E先生」(医师如此称唿他)开了一种名叫「氯米帕明」的抗忧郁剂,让他一天「只吹」3~4小时,副作用却难以忍受。当医师们拜访他家时,立刻就得面对「同一首歌吹不停,曲调清澈完美,几乎毫无间断」的状况。医师们开始探询E先生是否真的得了强迫症(译註: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简称OCD),但他向医师保证,自己吹口哨的强迫行为,并非受到沉溺的想法所驱使。「不过,如果别人要求他不要吹的话,他还真的会觉得很烦躁、焦虑。」
连强迫性吹口哨都有了,那强迫性挖洞有何不可?英国的「鼹鼠人」威廉‧雷托(William Lyttle),就有一种强迫作用,使他在伦敦东区的自家底下,挖出又大、又深、又迂回的隧道。这条隧道总长60英尺,有些还深及房屋(继承自父母)下方26英尺。他在2010年去世前不久,向记者如此表示:「一开始只是想挖个地窖,结果地窖变成两倍大。」地方政府当局害怕房子垮掉,只好把雷托赶出去,接着工程师从隧道里头,移出了三十三吨重的破瓦残砾,以及三台车、一艘船。
这种极端的疾患,或许会让人觉得强迫行为是别人家的事,只有极少数人需要担心这种精神病。但资料显示并非如此。史丹佛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科学家,在2006年的分析报告中发现,16%的美国成人(约三千八百万人)都曾有强迫购买行为,而且其中有2~4%(最多约九百万人)有囤积症(compulsive hoarding)。不管是在哪一年,我们之中都有1%的人饱受强迫症之苦,这种病可说是众多焦虑症中的黑暗王子。
至于有轻微强迫作用,也就是不严重妨碍健康、不足以被认定为精神病的人,甚至还更多;事实上,有些强迫行为还挺受用的,它们协助我们管理生活,或让工作更有效率(起码自己这么觉得)。你应该不太会认识口哨吹不停、挖隧道挖不停,或是断层扫描扫不停的人。但我敢跟你打赌,你应该认识不少人,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更夸张的是,某位干劲十足的作家经纪人,一动完开心手术就在找手机。我们的强迫行为轻微到没人发觉,必须更仔细观察才会发现。
你也可能认识像是艾美(Amy)这样的人——我在餐厅和她见面,当时她是神经科学系的研究生,也是强迫症支援团体的创办人。当我走近餐厅,并没有多看一眼这位站在73街转角的女性。我瞄到她的黑色秀发,觉得这位美女绝对不是我的会面对象,因为她要和我谈的是拔毛癖(拔毛拔过头,使患者变秃的症状)。
不过迟疑了一阵,她终于叫住我。「请问妳是雪伦吗?」「妳……妳是艾美?」
吃完主菜后,艾美说她从十二岁开始就会拔头发,她说:「这变成我缓和焦虑的方法。」她的压力来自于想在学业上表现优异,以及获得纽约某间明星理工高中的奖学金。她会戴帽子掩饰被拔秃的地方;十年来她放弃游泳,因为她无法克制自己拔头发,而且连腿毛与手毛都拔,拔到身上一根体毛都没有,全身像蛇一样光滑。尽管她因为拔毛癖而被嘲笑,但这种方法确实缓和了她无所不在的焦虑。「我被焦虑缠身,当它变强时,我就拔毛。这非常有效,让我恢复正常,从压力的顶层退到底线。」
在艾美的拔毛癖患者支援团体中,其中有位成员是警察,本来很爱打高尔夫,但不得不放弃。艾美说:「他每次看到握住球桿的手,就会去拔手背与手腕上的毛。」还有一位成员是拉比(译註:意指犹太教的学者),他整个人被罪恶感吞噬,倒不是拔毛动作本身所致,而是因为他在安息日工作(他认为拔毛也算工作!)——严格遵守规定的犹太人,连灯都不敢开。
虽然遍览这些极端的人类行为,总是让我很入迷(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好险这没发生在我身上」),但这些强迫行为的故事,给了我一个领悟:我在这些故事里,看到自己、家人、朋友与同事的阴影。我们或许没有活得很极端,但这些故事,阐明了人类行为光谱中,最广阔的中间部位——我们大多数人都身在其中。
这几年来,我为本书进行研究与报告,发现我们的所作所为中,有许多并非追求喜悦或满足好奇心,也不是出于责任感或自尊心,而是为了抑制焦虑——虽然这些行为不会被诊断为疾病。或许会留下旧书报,是因为少了它们,你的房间就像没了墙壁,让你备感紧张;或许埋首于一项专案,是因为这样才能缓和侵蚀心灵的焦虑——你担心若不这么做,就会有许多危险的事,发生在自己、家人与世界上。或许你採购杂货就和军事计画一般精准;或许你毛巾非这么挂不可;或许你做家事和编排芭蕾舞一样,连乔治‧巴兰奇(译註:George Balanchine,美国芭蕾舞之父)都会翻白眼。
推荐序一
或许,我们都需要一点点「强迫」
现代的人常常一空闲下来,就会拚命滑手机;朋友聚会时,往往不是交谈甚欢的景象,而是每个人都低着头看着手机萤幕。有些朋友甚至会在出门前,来回确认瓦斯有没有关、门有没有上锁。其实,这些接近强迫行为的状况,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只是程度轻重的差异而已。
多年以前,曾有一位女性强迫症患者,由她的丈夫陪同前来求诊。我细问之下才发现,最困扰这位女患者的行为,是她每天必须花五~六小时在洗澡这件事情上。每天从下班回家、做完晚餐、做完家事后,她就开始准备洗澡的种种仪式……。
右手扭开浴室的喇叭锁(这时右手脏了),进入浴室,手按压杀菌洗手乳(这时左手脏了),并打开洗手台水龙头,清洗双手。
褪去全身衣物(这时双手又脏了),彻底清洗双手。
右手挤压洗面乳(这时右手脏了),彻底清洗右手,洗脸。
右手打开莲蓬头开关(这时右手又脏了),再次彻底清洗右手。
右手按压洗发精瓶盖(这时右手脏了),再彻底清洗右手,再洗头。
右手按压沐浴乳瓶盖(右手脏了),彻底清洗右手,再洗上半身(没有衣物遮盖的部位要洗两遍)。
右手按压洗沐浴乳(右手又脏了),彻底清洗右手,再洗下半身(没有衣物遮盖的部位要洗两遍)。
千万别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接下来,则是用各种不同的清洁剂与用具,把浴室从地板到天花板(这不是形容词,真的包括天花板在内)刷洗、擦干。地板和墙壁每块磁砖与磁砖之间的缝隙,经过她经年累月刷洗的结果,不仅洁白如新,而且还向内凹陷几乎半公分。等到每天晚上完成这冗长的过程,都已经是五、六小时后的深夜了。
经过将近半年的心理治疗,患者终于顺利克服这恼人的强迫症。在治疗的过程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是患者的丈夫所付出的耐心与温柔。每週不间断的温馨接送情,加上对妻子的鼓励与包容。这对于「看惯」夫妻冷战热吵的我而言,无疑是一幅清新美丽的风景。
事情到此,原本是完美的终结篇……。
岂料,治疗完毕后过了一年,这位患者又回来找我。只不过,这次丈夫已经变成前夫,她摆脱了强迫症,却换来忧郁症。经过几次谘商后,这才釐清头绪。原来患者克服了强迫症之后,却逐渐对丈夫的嘘寒问暖感到厌烦。她则是多年以来首次感受到自由,经常下班后流连在外,弃丈夫于不顾,结果两人最终以离婚收场。
类似的案例始终让人迷惑:为什么病治好了,家庭却也散了?
有些家中有罕见疾病孩童的家庭,夫妻同心为小孩遍寻良医、筹钱治病。一旦孩子不敌病魔摧残,夫妻却以迅速离婚收场。难道这只能简单的用「共患难易,同享乐难」来解释吗?
或许正如本书作者书末的智慧之语:「许多行为之所以吸引我们去做,不是因为它们能带来喜悦,而是它们保证能平息焦虑。」这里指的焦虑或许也可能来自生活,等到焦虑平息了,隐藏在其下的问题,或许才是应该解决的课题吧。这不仅是对于强迫行为而言,或许也可以是针对生活而言。
我的朋友们,别再一味的敌视、抗拒强迫行为,而是应该反过来、试着理解冰山底下埋藏的焦虑,到底来源是什么?这也是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面向。
推荐序二
平和看待我们或多或少都有的「强迫行为」
这本关于强迫行为的新书,是美国资深科学专栏作家雪伦‧贝格利(Sharon Begley)的着作。她在书中洋洋洒洒的论述关于强迫行为的种种情况,在其活泼流畅的行文中,时见其独到的见解、批判的厚度。
书中也谈到许多关于强迫行为的情况,例如有位女患者总是会担心她的猫跑进冰箱里,即便她明知道这不太可能,但却受不了大脑里头不断呢喃的声音,而一次又一次跑去检查。或是像网球明星纳达尔会用只有自己知道的仪式放水瓶,以特定的顺序拿毛巾。
我个人在临床心理的专业虽不是在强迫症领域,过去主要的临床经验,是在大学辅导中心接触过的大学生或研究生,这些学生中有些饱受强迫症的困扰,而来求助。在有限的临床经验中,我主要以传统心理病理学中讨论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来看待他们所身处的困境,并提供协助。
状况严重者,透过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及社会支持,我发现难度虽高,但若能积极持续前来,问题是能逐渐缓解。状况较轻微者,在心理治疗的持续工作中,我也发现他们一旦有了「悟性」后(也就是认知行为治疗常说的想法改变),他们会开始讶异,为何这强迫意念或强迫行为,在治疗前如此难以撼动?而强迫性的意念及行为,若在一定的适应范畴内,反而是成就的重要来源。试想哪位优秀的艺术家、作家、建筑师、学者专家等,没有这样的思考及行为特质?若放大将其当作向度(dimensional)而非类别(categorical)的角度来看心理病症时,则会有很不一样的理解。
本书的作者,就是将类别化的强迫症,扩大成向度化的强迫行为或强迫心理现象,前者是窄狭的病理探究,后者则是普罗大众的心理状态,这样的思维使得她的写作格局,可以悠游于传统到当代的脑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甚至宗教文化学的角度来切入探究;也让我们了解,或许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强迫行为,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有了这样的历史纵深能耐,又能以新闻记者人物採访的专业,直击一些关键学者、病人或病人家属的对话(注意,许多有强迫行为的人,常常又是大明星、大选手等等),来贯穿在整本书的文字中,使得本书读来令人兴味盎然,充满趣味与启发性。
我个人喜欢作者说:「强迫行为平息各种大小焦虑的能力,其实是大脑赐予我们最棒的天赋之一。」我想都值得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反覆去想:身而为人,我们该怎么不带评价的,看待我们多多少少都有的「强迫」!
图书试读
网球巨星拉斐尔‧纳达尔(Rafael Nadal)比赛时,会依照只有自己知道的仪式摆放水瓶;以特定的顺序拿取毛巾;用略带蹒跚或拖曳的方式调整步伐,避免踩到球场的线;然后在发球前拉一下短裤。比赛换边时,选手都会坐在边线的座椅上稍微休息,此时纳达尔会拚命抖脚,好像要把蚂蚁抖掉一样。接着他会以之字形路线走回场上,在底线像袋鼠一样跳来跳去。就像一个有强迫型人格的凡人,想用疯狂规则掌控自己的世界。
不管是捕鱼、在洋基球场主投,还是在历史最长、最具声望的温布顿网球赛出赛,仪式的力量、甚至合理性,都源自于控制感,并且给予实施者自信,这些都能转化成更好的表现。渔夫相信自己的护身符与咒语,能保护他不被凶勐的海浪吞没;由此而生的控制感与自信,让他面对风浪时,不会被过度震慑,也因此更能保护自己。一位相信鸡肉晚餐有神力的打者,或许看球能看得更清楚,安打也就一支接一支。
我的仪式,对你来说却是强迫行为
在某些特定背景下,强迫行为不只和病态搭不上边,还司空见惯,因此没受到注意。我们称它们为文化仪式。如果你不是处在某个根深蒂固的文化之下的局外人,那么该文化的仪式,对你来说就有种……嗯……病态的趣味;你甚至会把它们视为强迫症的表现,就和1990年代的研究人员一样。
美国人类学会的期刊《风气》(Ethos),在1994年刊载了一份极具影响力的论文,其中希里‧杜兰利(Siri Dulaney)与艾伦‧佩吉‧费雪(Alan Page Fishe)就主张:「仪式的特征,也能用来定义一种精神病,亦即强迫症。仪式与强迫症之间,存在着一种共通的心理机制。」的确,文化和宗教仪式,与强迫行为者进行的仪式扯上关系,可以追溯到佛洛伊德,他主张这两种个案都一样,只要当事人不进行仪式,就会感到不安,而且对执行仪式抱持极度的尽责性。杜兰利与费雪提到:「仪式本质上就让人难以抗拒。」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书名充满了智慧和洞察力,“每个人都有「不做,就很难过」的事”,这句话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对自身行为模式的审视。我一直认为自己的某些习惯是“强迫”,是需要克服的,但这本书却提出,这些“强迫行为”可能恰恰是“有所成就的人”的特质之一。这让我瞬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常常观察身边那些在各自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的人,他们身上总有一种异于常人的专注和坚持,有时候甚至会表现出一些常人难以理解的“固执”。这本书会不会揭示,正是这些“固执”或者说“强迫”的特质,让他们能够在追求目标的道路上披荆斩棘,不受干扰?我迫切想知道,作者将如何阐述这种“成就与强迫行为”之间的联系。是说那些成就斐然的人,恰好拥有某种程度的“健康型强迫”,让他们能够高度聚焦,精益求精?还是说,他们只是能够巧妙地利用并转化了这些潜在的强迫倾向?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不再仅仅看到强迫行为的“负面”一面,而是去探索它可能存在的“正面”功能,甚至与成功挂钩。
评分读到这本书的书名,脑海中立刻闪过无数个“我就是这样”的瞬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怪人”,有着各种各样不合常理的坚持,比如,下班回家后,必须先花半小时把一天穿过的衣服按颜色和材质叠好放进衣柜,否则就觉得心里不安;或者,在开始写一个重要报告之前,必须先把电脑里的所有图标整理一遍,确保桌面干净整洁。这些行为,在我看来,只是我个人的“小癖好”。但这本书的名字《强迫行为的心理学:每个人都有「不做,就很难过」的事》以及副标题“有所成就的人,都有自己的强迫行为”,瞬间让我意识到,或许这些“癖好”并非毫无意义,甚至可能是一种“成就的密码”。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够深入探讨这些行为的心理机制,它们是如何在我们的大脑中形成的,以及为什么有些人能将其转化为驱动力,而有些人却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作者是否会分析一些具体的案例,让我们看到不同类型的“强迫行为”是如何在现实中影响人们的生活,以及如何与个人成就相辅相成?这本书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一种重新认识和理解自身行为的可能性,将曾经被视为“怪癖”的东西,置于更广阔的心理学视角下审视。
评分拿到这本书,第一感觉就是它的切入点非常独特且贴近生活。我们常常听到“强迫症”这个词,但多数人可能将其与严重的精神疾病划等号,而这本书却把目光聚焦在“每个人都有”的层面,这点就足以吸引人。我一直对那些看似生活规律、一丝不苟的人感到好奇,他们是如何做到如此自律的?是天生的性格使然,还是后天某种心理机制的训练?书中提到的“狂洗手、勐整理、囤积、做完特定仪式才开始”这些例子,虽然有些听起来夸张,但仔细想想,我们自己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仪式感”或者“非做不可”的倾向。比如,我写邮件前一定要先通览一遍,确定逻辑清晰,否则无法下笔;或者在开始一项新任务前,会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去整理文件,好像不这样做就无法集中精神。这本书的价值可能就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正视并理解这些行为,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坏习惯”。我希望作者能够提供一些案例分析,让我们看到不同类型强迫行为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以及它们对个人生活和工作可能产生的影响。
评分这本书的标题,尤其是“每个人都有「不做,就很难过」的事”,瞬间就击中了我的痛点。我一直认为自己有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比如,每次出门前都要反复检查门锁是否锁好,有时甚至要锁三次以上才放心;或者,在工作过程中,一旦被打断,就必须从头开始整理思路,否则会觉得非常焦虑。我曾一度认为这些是自己的“怪癖”,需要努力改掉。然而,这本书却提出,这些“强迫”的行为,可能恰恰是“有所成就的人”所共有的特质。这个观点让我眼前一亮,充满了好奇。我迫切想知道,作者将如何解释这种联系。是否是说,那些成功人士,正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定程度的“专注”或“仪式感”,才能够排除干扰,全身心地投入到目标之中?或者,他们只是学会了如何利用这些潜在的“强迫”倾向,将其转化为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不再仅仅将“强迫行为”视为一种需要克服的障碍,而是去探索它可能存在的积极意义,甚至将其与个人成长和成就联系起来。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深入剖析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逻辑,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以及理解那些在各自领域闪耀的人们。
评分这本书的标题就抓住了我,"每个人都有「不做,就很难过」的事",这句话太有共鸣了!我一直以为只有少数人会有这样奇怪的行为模式,但作者似乎在暗示,这种“强迫”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普遍得多,甚至与成就挂钩。这让我对接下来的内容充满了好奇。我个人生活中就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比如出门前必须检查所有电器是否关闭,否则就会心神不宁。还有,工作时桌上的物品必须摆放得整整齐齐,否则效率会大打折扣。我总觉得这些是我的“怪癖”,但如果这些行为背后有更深层的心理学解释,甚至与成功有关,那将是一次颠覆性的认知。我期待这本书能深入剖析这些行为的根源,它们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利用这些行为驱动自己取得成就,而另一些人则可能因此感到困扰。作者是否会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强迫行为的表现差异?或者,是否存在一种“健康的强迫”和“不健康的强迫”之分?我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看看这本书能否帮助我理解自己,以及理解身边那些看似“固执”甚至“偏执”的朋友和同事。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