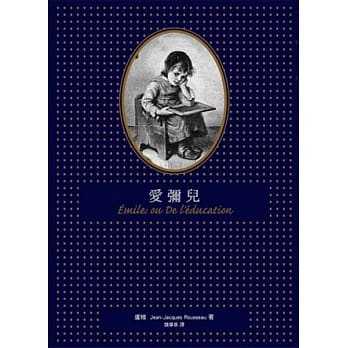具体描述
没有「超人」思想,〈斗阵俱乐部〉〈骇客任务〉〈蝙蝠侠〉〈黑暗骑士〉就失去了主题;
即便是〈银翼杀手〉〈心灵捕手〉〈楚门的世界〉〈蓝丝绒〉
〈神鬼认证系列〉〈前进高棉〉〈谋杀绿脚趾〉……都深埋着尼采的意念。
请听,查拉图斯特拉怎么说!
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查拉图斯特拉说:「上帝已死,人类当成为超人。」
新约圣经中的耶稣,成为肉身的神,来到世间对众人传递天国的福音。
孤独的查拉图斯特拉也下了山,想把光带入人世,而他传递的会是什么「福音」?
「瞧,我是教你们做超人!
人是应被超越的。你们为了超越自己,做过什么事呢?
不要相信那些跟你们侈谈超脱尘世的人,人类的幸福,应当是肯定生存本身!」
动物是道德的奴隶,超人是道德的主人。至于人,是联结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悬在深渊上的绳索。
走过去是危险的,停在半空中是危险的,回头看是危险的,战慄而停步是危险的。
但人之所以伟大,乃在于他是桥樑而不是目的;人之所以可爱,乃在于他是过渡。
查拉图斯特拉为了拯救过去属于动物的人们,也为了肯定走向超人未来的人们,他干犯神怒而灭亡,他甘愿因现在的人们而灭亡。
人们说尼采疯了,但一个深知自己被视为疯子的人,是真疯吗?尼采就是查拉图斯特拉,他看到了繁华顶峰的人类文明,正随时准备坠入深渊,等待绝地的反转。而他的任务,就是启动这爆炸性的翻转。
他是先知。
而先知是孤独的。
先知总被视为疯子。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乃集尼采重要思想之大成,透过哲学家查拉图斯特拉的流浪及教导,以「永远回归」、「上帝已死」及「超人」来阐述并回答这个问题。人的生命是既是无限回圈,神又早已离开,人的一切活动和生存意义就要自行掌握和创造。命运无可抗拒,摆脱了神的人类要如何独自面对这悲剧式的处境?人应摆脱动物(猿猴)的状态,以态度和意志来决定自身存在的意义,从人类的过渡阶段,走向超人。
名人推荐
「尼采对于自己的洞察,比过去任何人都更透彻,未来也不太可能有人企及。」——佛洛伊德
「很少人要为了自己的天才付出这样重大的代价。」——威尔.杜兰(Will Durant)
著者信息
翻转西方传统精神、对所有价值进行重估、独立自由的极致追求者──尼采。
尼采动笔写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那年他39岁。2年后他完成此书,再过4年便精神崩溃。
然而他一向深知,是自己的先知性格注定了自己孤独的路,也注定了被视为疯子、被世人所赠恶。「这就像把一颗星投入荒凉的空间和冰块一样的孤独的气息里。」「你超越过他们往前走……他们为此对你大为不满……他们为此决不饶恕你。」(《查》第一部)
很多人误解尼采的思想是出于对世人的憎厌和生命的虚无。然而,他比其他人更爱着世人,他比其他人更热烈拥抱着生命。
「我的弟兄,带着你的爱和你的创造力走进你的孤独里去吧;以后,公正才会一瘸一拐地跟着你。
我的弟兄,带着我的眼泪走进你的孤独里去吧。我爱的是那种想超越自己去创造而由此毁灭的人。」(《查》第一部)
他厌弃的是被他者道德辖制的生命状态,因此他要成为先知,宣讲超人的福音,把世人从奴隶状态救拔出来,要人成为自己的主人。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乃集尼采重要思想之大成,透过哲学家查拉图斯特拉的流浪及教导,以「永恆回归」、「上帝已死」及「超人」来阐述并回答这个问题。人的生命是既是无限回圈,神又早已离开,人的一切活动和生存意义就要自行掌握和创造。命运无可抗拒,摆脱了神的人类要如何独自面对这悲剧式的处境?
译者简介
钱春绮
中国文学名译家,译过《浮士德》、《歌德诗集》、海涅《诗歌集》、波德莱尔《恶之花》等。荣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鲁迅文学奖,其译作被认为是德国文艺翻译的佼佼者。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当代最有名的中译本,有孙周兴的译本(以尼采全集考证版KSA所译出)、黄明嘉和娄林合译的译本(以尼采全集考证版KSA为底本,同时纳入Puetz版的注解以及英、法译的译注),以及钱春绮的译本(根据Goldmann Klassiker的)版本)。前两个译本考证详尽,也有编码,适合学术研究之用,是哲人的译本。
钱春绮作诗、译诗,也是德国文学研究者,译笔神采飞扬又极尽忠于原文,是诗人的译本。注释解释了许多德文原文的意涵、双关、典故,以及跟《圣经》《浮士德》有关的互文、戏仿,对于不熟悉相关语文、文学、思想背景的一般读者来说,相当有帮助。
图书目录
繁体中文版导读(刘沧龙)
第一部
查拉图斯特拉的前言
查拉图斯特拉的说教
三段变化
道德的讲座
背后世界论者
轻视肉体者
快乐的热情和痛苦的热情
苍白的犯罪者
读和写
山上的树
死亡的说教者
战斗与战士
新的偶像
市场的苍蝇
贞洁
朋友
一千个目标和一个目标
爱邻
创造者的道路
年老的和年轻的女人
毒蛇的咬伤
孩子和结婚
自愿的死
赠予的道德
第二部
拿着镜子的小孩
在幸福的岛屿上
同情者
教士们
有道德的人
贱民
塔兰图拉毒蛛
着名的哲人
夜歌
舞蹈之歌
坟墓之歌
超越自己
崇高的人们
文化之国
无玷的认识
学者
诗人
重大的事件
预言者
拯救
处世之道
最寂静的时刻
第三部
浪游者
幻影和谜
违背意愿的幸福
日出之前
变小的道德
在橄榄山上
走开
背教者
还乡
三件恶行
重压之魔
古老的法版和新的法版
康复者
伟大的渴望
另一曲舞蹈之歌
七个印
第四部
蜂蜜供品
求救的叫声
跟君王们对话
蚂蟥
魔术师
失业
极丑的人
自愿的乞丐
影子
正午
欢迎会
晚餐
高人
忧郁之歌
学问
在沙漠的女儿们中间
觉醒
驴子节
醉歌
预兆
译后记
图书序言
阅读尼采的理由——成为你自己
尼采之所以如此与众不同,不是天赋异禀,也不是刻意追求特立独行,而是忠于自我。
其实,每个人生来都是与众不同的,但是我们却因为害怕孤独、害怕失去他人肯定,最终失去了自我。一个人不能肯定自我,不论获致多大的成功,最后都只是虚浮的空中楼阁。
我们为什么无法自我肯定?何以无法建立自己的价值尺度并依此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尼采给我们的示范是,唯有忠于自己的自由精神,才能自主、坦荡、无畏地听从内在的声音,建立坚实的信念,进而打造自己、超越自己、创造价值。唯有看重自己的人,才能受人尊重,才能明白人的尊严与价值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们阅读尼采的理由,或许就如尼采自己所说,不是为了追随他,而是要追随自己。作为自由独立的精神典范,尼采的思想可说是当代的精神标记。欧洲自启蒙运动以来所追求的独立自主、自由精神,在尼采身上达到颠峰,而且启发了二十世纪各种前衞思潮,至今动力未减。
上帝已死,人类该走向何方?
尼采身后已一百多年,他的自由思想是否仍有尚未深掘的矿藏值得继续开採?《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这部着作有何独特性?提出了什么思想?对于现实生活有何具体启发?
尼采的书写与生活,以独特的方式重新定义了哲学,他翻转了欧洲的精神与价值传统,而且甚至要「重估一切价值」。欧洲传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要翻转?要往什么方向翻转乃至重新确立价值标准?
尼采所提出的巨大问题与回应方案,翻搅了西方思想世界,甚至对欧洲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产生巨大影响。他认为,人类文明登上繁华的顶巅,却又随时准备坠入深渊。这个世界已经走到虚无主义的尽头,正等待一次绝地反转,而他的思想就是引信,为的就是启动此一爆炸性翻转。
查拉图斯特拉说:「上帝已死。」(Gott ist tot.)失去地平线的人类,在无重力的空茫中会堕落何处?上帝之死,宣告的是人类应该扬弃绝对真理的束缚,不再做道德的奴隶,而是成为道德的主人。在这没有圣哲神佛的时代,命运由人类自己掌握,不再盲目追随。然而,在没有圣哲神佛的时代,孤立险峰的当代人真的足以承担自身的命运?我们又可知该往何方启程?尼采要我们跟随自己、超越自己,但是成为能自我超越的「超人」(Übermensch),是否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尼采最着名的宣言「上帝已死」,首先是在更早之前的着作《快乐的科学》(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借疯子之口说出的。疯子诞妄不经的说词充满丰富的寓意,也是理解「上帝已死」的重要背景。以下引录最关键的段落:
疯子唿叫着:「上帝去哪儿了?让我来告诉你们,我们把他杀了——你们和我!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兇手!但我们是怎么办到的呢?我们怎能把海水喝光?谁给了我们海绵让我们擦去了地平线?当我们把地球从太阳的锁链中解开,我们要怎么办?现在地球要去哪儿?我们要去哪儿?离开所有的太阳吗?我们会一直下坠吗?向后方、向旁边、向前方、向所有的方向坠落?还有所谓的上下之分吗?我们不就像穿越无尽的虚无般惶惑吗?虚空不对着我们唿气吗?不是更冷了吗?随之而来的将是无尽的黑夜?大白天不是得把灯笼点着吗?我们还没听到那些埋葬上帝的掘墓人的吵闹声吗?我们还没闻到神圣的腐臭吗?──连上帝也会腐臭。上帝死了!上帝永远死了!而且是我们把他杀死了!我们这些兇手中的兇手要怎么抚慰自己呢?那最神圣、最强大、迄今一直统治世界的,竟血溅我们的刀下──谁可以拭去我们身上的血迹?用什么样的水才能将我们洗净?我们必须发明怎样的赎罪庆典和神圣戏剧?这个伟业对我们而言岂非过于伟大?难道不是必须我们自己成为上帝才足以与之匹配?从来就未有比这个更伟大的行动了──而我们的后代也因为这个伟大的行动之故,将生活在比迄今所有历史更高的历史阶段。」
疯子这时停止说话,再看着他的听众,他们也沉默而诧异地看着他。最后,他把灯笼摔在地上,灯碎火熄。然后他说:「我来得太早,来得还不是时候。这个非凡的大事还在过来的路上──人们还闻所未闻。闪电和雷鸣需要时间,星光需要时间,行动需要时间,行动完成后被听到、被看到也需要时间。这个行动对他们而言太过遥远,比最远的星球还远──然而他们却完成了此事。」
一个具有超前意义的行动很容易遭到误解,因为世人仍然以旧的理解框架来看待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上帝已死」似乎是个陡然现身的大事件,却早已潜伏在历史深流之中,只是人们一直未曾察觉。即便上帝之死这个事实浮出表面,且几乎已是昭然若揭,世人仍旧浑然未觉。因此,当有人指出国王没穿衣服的事实,便被视为疯子。而尼采,就是那太早出世、预先瞥见历史真相的疯子。
「上帝已死」的断言,表征人类认识能力已然进展到关键的一步,也就是发现任一宗教与形上学对世界所作的说明,都不具备绝对的有效性。对世界的所有阐释,都脱离不了人的眼光、人的生存需求,以及人的限制。尼采引用路德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倘若没有明智的人,上帝无法自存。」同时又加码表示:「倘若没有无知的人,上帝更难存在。」如果,人类真是为了寻找自身存在的依据而造了上帝,那么,人类一旦发现自身的存在并不具必然性,上帝的存在也将失去必然性。传统宗教与形上学预设为无条件存在的上帝,在疯子尼采的眼中成了有条件者,而上帝存在的条件竟然是人类生存的需求!
尼采不只怀疑上帝的存在,他甚至怀疑绝对真理的存在。什么是真理?尼采说:「对人类而言,无法驳倒的谬误就是真理。」倘若这个世界并没有上帝或某个绝对真理在操纵,那么尼采如何描述我们所存活的世界?
永恆回归,流变的生命状态
我们活着,没有超越者预先指定的目的,而是在没有预设意义的状态下,赤裸裸地经历各种生灭变化。这变化不断迎面而来,且一刻不止,只是我们平常视而不见,或忘记一切都在变。尼采提出「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之说,一方面要说明这个世界所处的流变状态,另一方面则试图立足于人的生存立场来回答:如何在自然流变的生命当中获得生命的自主权力?
这需要生命的自我关照与转化。「生命」就是有机体活动变化的历程,因此也随时面临生命的自然来去。我们身边重要的人乃至自己终将离开人世,这是必然之事,但不必为此终日悬念而自苦,而是要练习迎向这些必然发生的事,然后向有智慧的人学习生命完成之道。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这样一部智慧之书,而且是一再映照着《圣经》福音书的智慧之书。这个智慧并不仰赖先知的神启,也不寄望终极的救赎,而是像书中的主角查拉图斯特拉一样,在追寻生命的孤独历程中,几经挣扎而获致自我超越与自我肯定。或许到了最后,死亡也是一件受到祝福之事。还好我们会老、会死,否则不懂珍惜生命;因为知道身边的人有朝一日会与我们永别,所以会珍惜看重。这都是死亡与分离教给我们的智慧,所以要感谢死亡,让我们明白分离所带来的痛苦和意义。倘若我们对分离无感,对生命消亡无所谓,那样的生命才可怕。
如此看来,担忧死亡带来的痛苦是件好事,但不要过度沉迷于痛苦,而要学系抽身出来,看看我们还有的一切,并对此感激祝福。生死不是界限,生的每一刻都包含了死的可能性;死也不可怕,因为死和生有个微妙的连系需要我们去参透。有智慧的人就能参透这点,所以能对生命有情而不沾滞,让该来的来,该走的走。
从流变的观点来看生命,那么生命便是在生和死、上升和下降、起点和终点之间流动循环的过程,生无可乐、死无可悲,流变不已的自然世界也无善恶可言。尼采以「永恆回归」(ewige Wiederkehr)的意象式概念表达出流动的世界和生命的循环之道。如果我们把线性展开的时间理解为从起点迈向终点的历程,那么「永恆回归」则表示,生命之流的终站便是回到起点。如此看来,自我完成之道便是成为自己的过程,走向死亡不是到达终点,而是迈向重生的起点。我们可以悲观地说,生命的流变使得一切都是徒劳的;然而我们也可以从肯定的态度来看,即使最后一无所获,仍要庄严地奋斗,这才就是对生命价值的最高肯定与无限礼赞。尼采既能体认虚无主义悲观的一面,又像悲剧英雄一样热烈地肯定生命的自我完成之道,也因此超越了虚无主义。
本书译者钱春绮先生(1921-2010)是着名的译家,毕生以译事为职志,对德语文学的翻译贡献卓着,素为译界推崇。钱先生翻译时根据的德文版本是Goldmann出版社1984年的版本,在译后记中他表示还参考了R. J. Hollingdale的英译,并提及Hollingdale这位着名译家对于翻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感到困难重重。尼采的语言与思想都显现了强烈的艺术特性,喜用隐喻、寓言、戏仿、反讽的方式表达另类的思考,这本诗化的哲学着作尤其如此。因此即使是翻译成与德语同一语系的英语,都让译家力有未逮,更何况是翻译成非拼音系统的中文了。多亏钱春绮先生已有翻译歌德等德语文学家着作的丰富经验,丰厚的语文素养与严谨精确的译笔,已不仅足以因应一般读者之需,就尼采研究在学术引用来说也有参考价值,可说是中文世界爱好尼采思想读者的「福音」。
刘沧龙 2014/5/20 于德国法兰克福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副教授)
图书试读
1 [1]
查拉图斯特拉三十岁时[2],离开他的家乡和他家乡的湖,到山里去。他在那里安享他的智慧和孤独,十年不倦。可是最后,他的心情变了,─────某日清晨,他跟曙光一同起身,走到太阳面前,对它如是说道:
「你伟大的天体啊! 你如果没有你所照耀的人们,你有何幸福可言哩!
十年来,你向我的山洞这里升起:如果没有我,没有我的鹰和我的蛇[3],你会对你的光和行程感到厌倦吧。
可是,我们每天早晨恭候你,接受你的充沛的光,并为此向你感恩。
瞧! 我对我的智慧感到厌腻,就像蜜蜂採集了过多的蜜,我需要有人伸手来接取智慧。
我愿意赠送和分发,直到世人中的智者再度乐其愚,贫者再度乐其富[4]。
因此我必须下山,深入人世:如同你每晚所行的,走下到海的那边,还把你的光带往那下面的世界,你这极度丰饶的天体啊!
我必须,像你一样,下降[5],正如我要下去见他们的那些世人所称为的没落[6]。
就请祝福我吧,你这宁静的眼睛[7]。即使看到最大的幸福,你也不会嫉妒祝福这个快要漫出来的杯子吧,让杯里的水变得金光灿烂地流出,把反映你的喜悦的光送往各处!
瞧! 这个杯子想要再成为空杯,查拉图斯特拉想要再成为凡人。」
─────于是查拉图斯特拉开始下降。
注1
查拉图斯特拉在长期孤独之后,精神充沛,想下山前往人世间,做个像太阳一样的施予者。
注2
〈路加福音〉3,23:「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
注3
鹰象征高傲,蛇象征智慧。
注4
智者抛弃他的智者意识,自觉自己的无知,而成为受教者, 故能乐其愚。贫者的心感到有受教的必要而豁然开朗,这就是他的富有。换言之,即智者和贫者都乐于接受查拉图斯特拉的教言。
注5
「下降」原文unter-¤gehen( 名词形: Unter-¡ gang), 此处指下山, 但此字有多义,又指太阳的下落、下沉,暗指查拉图斯特拉迄今的生活告一结束而转变,超越他的故我, 故亦含有越过去之意。此外,这个字在德语中还有没落、毁灭之意。
注6
从高处往低处下去,通常对此字认为含有贬意。世人把untergehen 当作「没落」,而查拉图斯特拉则否, 他认为「下降」到人世间,是奉献自我,不考虑自我。
用户评价
這本「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詳注限量精裝本)」我真的等了很久,終於收到手了!開箱的那一刻,紙質的溫潤手感、封面燙金的細緻紋路,還有書脊那種紮實的精裝感,立刻就讓我覺得這是一本值得珍藏的書。不是那種隨處可見的平裝本,它有種沈甸甸的分量,彷彿本身就蘊藏著無盡的智慧。我平常就對哲學思辨很有興趣,尼采的名字更是如雷貫耳,但總覺得直接啃原著有些吃力,這次看到有詳注的版本,心裡就覺得非常踏實。從外觀上來說,這絕對是送禮自用兩相宜,而且限量精裝版這個標籤,也讓人感覺到一股獨特且珍貴的氛圍,彷彿擁有了某種稀有的寶藏。我迫不及待想翻開,感受書頁間傳遞的哲學力量,那種沉浸在文字世界裡的滿足感,絕對是無可取代的。
评分這本「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詳注限量精裝本)」一到手,就讓我愛不釋手。從外觀設計到內在的印刷細節,都透露著一股精雕細琢的誠意。我一直以來都對思想深度極高的哲學書籍抱持著高度的興趣,而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更是其中一顆璀璨的明珠。然而,作為一個非哲學專業背景的讀者,我常常在閱讀時感到力不從心,深怕錯過其中精妙的含義。這次的詳注限量精裝本,無疑為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契機,讓我能夠以更扎實、更清晰的方式去理解這部偉大的著作。那份精裝的厚重感,以及書頁翻動時帶來的細膩觸感,都讓我感受到這本書的獨特價值,是一本值得我細細品味、反覆研讀的珍藏之作。
评分收到這本「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詳注限量精裝本)」的當下,我的心情就像是發現了一個失落已久的寶藏。它的重量、厚度、還有那種精緻的裝幀,都散發出一種低調卻極致的質感。我特別喜歡它使用的紙張,觸感溫和,油墨印製清晰,即使在昏黃的燈光下閱讀,也不會感到刺眼。這本書不僅僅是一本讀物,更像是一件藝術品,擺在書架上,本身就是一道風景。作為一個長期關注哲學和文學的讀者,尼采的作品一直是我的必讀清單,但礙於時間和專業知識的限制,總是希望能有更貼近讀者的版本。詳注版的出現,讓我看到了深入理解這本巨著的希望,不用再擔心被艱澀的詞彙和深奧的概念所阻擋。這份精裝本的出現,無疑為我的閱讀體驗增添了更多期待和儀式感。
评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詳注限量精裝本)」在我手中,是一種沉甸甸的滿足感。它的裝幀質感,絕對是市面上少見的。觸摸那精緻的封面,感受著紙張的紋理,你會發現這不只是一本書,更是一份對知識的敬意,對經典的呵護。我一直以來都對哲學探討著迷,尼采的名字更是迴盪在許多思想家的論述中,但對於《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這部被譽為他思想結晶的作品,我總覺得需要一個更友善、更易於深入的引導。看到「詳注」這兩個字,我彷彿看到了一盞明燈,能夠照亮我前進的道路,讓我不再迷失在複雜的哲學迷宮裡。這本限量精裝本,絕對是我書架上極為珍貴的一員,它承載的不僅是文字,更是對智慧的渴求與對完美的追求。
评分拿到「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詳注限量精裝本)」的瞬間,我立刻被它極具質感的包裝所吸引。那種紮實的觸感,精緻的細節,無不彰顯出其非凡的品味。作為一個長期以來對哲學思想,尤其是尼采這樣富有前瞻性哲學家的作品充滿好奇的讀者,這本詳注版的出現,無疑是我期待已久的。過往閱讀時,常常會被晦澀難懂的概念所困擾,而詳注版的設計,則像是一把鑰匙,能為我解開那些深藏的智慧之門,讓我能夠更順暢地進入尼采思想的殿堂。這不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份精緻的禮物,承載著豐富的知識與深刻的思考,我相信它將會是我書架上一件極為珍貴的擺飾,也是我心靈成長的寶貴夥伴。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