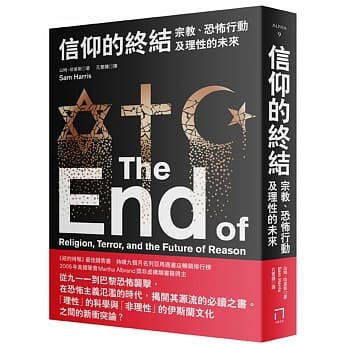具体描述
我们除了被动地面对、坐等犯罪案件发生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社会有没有可能改变与生俱来的恶?
「心理变态是什么?」
一个心理变态可以伪装出关心他人或充满悔意的样子,但是他的大脑却会说实话。
无差别杀人、暴力氾滥成为新兴的社会现象?
为何有些人要透过伤害或操控陌生人而发洩情绪、获得快感?
那些令人悲愤、恐惧又扭曲的行为,是否有可能被制止,甚至消灭?
这本书将带领我们探索变态犯罪的起源——大脑与基因,
也给社会一个刺激和思考:邪恶有可能是「天生」的,
而我们除了被动地面对、坐等犯罪事件发生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后天的环境,是否有机会改变与生俱来的恶?
詹姆斯‧法隆,一个被媒体报导评为成就卓越的科学家,他长期研究心理变态者的大脑,发现这些人都有着异于常人的脑部结构;但在2005年,他意外看见自己的大脑图像跟这些心理变态者的一模一样——研究发表在即,但这代表他要公开证明自己也是一个心理变态?
更惊人的是,当他回溯家族史之后,才知道四百多年来,这支家族充满了抛妻弃子的无情之徒,以及冷血兇残的杀人犯!他天生自带暴力基因,距离邪恶的岔路只有一步之隔,但为何最后成为备受赞誉的科学家?一个从心理变态中诞生的天才、狗血离奇的真实人生,执笔写下一段幽默励志的自我探索历程!
震撼推荐(依姓氏笔划排序)
天下独立评论专栏作家/「一个分析师的阅读时间」作者 Sean Huang
彰基司法精神医学中心主任 王俸钢
律师 吕秋远
台大法律学院教授 李茂生
精神科医师 沈政男
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 洪兰
国立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助理教授/泛科学专栏作者 黄贞祥
新闻工作者 黄哲斌
杜克─新加坡大学脑神经科学系助理教授 谢伯让
震撼推荐
「天性说明我们可能是谁,却无法决定我们该成为谁──选择,永远比基因重要。如果詹姆斯‧法隆拥有杀人犯的大脑都能成为神经科学家,你还有什么人生目标达成不了?」──天下独立评论专栏作家/「一个分析师的阅读时间」作者 Sean Huang
「这是个震撼人心的真实故事:一位备受尊敬的脑科学家,原来也有像心理变态一样的脑袋,而且祖上还盛产杀人魔,那为何他反而成了一位杰出的学者?这值得近年频频出现无差别杀人事件的台湾社会思考,这些悲剧背后究竟存在了什么样的系统性原因?我们的社会又该如何预防呢?」──国立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助理教授/泛科学专栏作者 黄贞祥
国际推荐
「《天生变态》感人至深,讲述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发现自己是心理变态者的故事。詹姆斯•法隆毫不避讳地谈及自己生理上的罪恶,以此获得赦免。我对这本书爱不释手。」──保罗•札克博士(Paul J. Zak),《道德博弈》的作者
「仅仅是『心理变态』这个词就能吸引任何人的注意,它也给数十年来的电影和电视剧集提供了灵感。事实上,我认为这个词本身并未包含其无穷的行为特质,无论好坏。在这本书中,法隆带我们深入他的精神世界,穿过错综复杂的旅程,打破所有关于心理变态行为的刻板印象。」──西蒙•米兰(Simon Mirren),「犯罪心理」(Criminal Minds)编剧和制作人
「自我探索的历程发人深思。法隆将自身置于显微镜下,试图釐清塑造其人生的生物和成长发展史。他的洞见迫使我们思考先天与后天的重要作用,以及适应性人格特质和不适应人格特质之间的隐密界线。」──约翰•伊甸博士(John F. Edens),德州农工大学人文学院心理学教授、临床培训主任
「本书窥视大脑的黑暗面,引人入胜。最阴暗的想法为什么会产生?有多少人处在心理变态者的状态,自身却并没有意识到?想要了解这些问题的人,绝不可错过这本书。法隆博士研究我们的大脑,帮助我们理解那些最奇怪的思想和行为是如何形成。鲜有人能像法隆博士这样理解大脑,并写出如此风趣而迷人的作品。真令人叹服。」──艾利•罗斯(Eli Roth),作家、导演和制片人
著者信息
詹姆斯•法隆(James Fallon)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教授、获奖的神经科学家。他研究的课题非常广泛,包括:成人干细胞、中枢神经系统回路、多巴胺、思觉失调症、帕金森氏症和阿兹海默症、人类大脑造影等。他的新创公司NeuroRepair获得了年度生物新技术的评选,推动干细胞研究的重大突破。
媒体报导他对产后新神经元发育的探索,是大脑研究十年来重要、惊人的成就。他经常为各类媒体提供犯罪心理的专业分析,曾在美剧「犯罪心理」(Criminal Minds)饰演本人。2008年,他受邀在Ted发表「探索杀人犯的大脑」演讲,揭开自己的变态家族史,引起热烈关注。
审订者简介
陈永仪
美国罗格斯大学健康心理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组织心理学硕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系学士。曾任教于美国西点军校行为科学及领导力学系 ,美国纽约大学与纽约市立大学心理学系。目前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主要研究包括压力、情绪与犯罪心理学。
译者简介
瞿名晏
现为专职翻译工作者,热爱音乐和心理学,阅读大量心理着作。
图书目录
【推荐序】爱让人不会成为魔鬼 律师 吕秋远
【推荐序】心与脑的双重自剖 精神科医师 沈政男
【推荐序】命定与命运的对抗 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 洪兰
【震撼推荐】
【自序】一场疯狂大脑的探险之旅
Chapter 01 一张脑部扫描图引起的混乱/
Chapter 02 成长之路:那些不起眼的「罪恶」/
Chapter 03 我是谁:科学家vs心理变态/
Chapter 04 充满血腥的家族史/
Chapter 05 变态大脑的现实成功之谜/
Chapter 06 从TED到「犯罪心理」/
Chapter 07 爱情、友情和那些不堪回首的韵事/
Chapter 08 其实我还有躁郁症/
Chapter 09 你能改变一个心理变态吗?/
Chapter 10 心理变态存在的必要性/
鸣谢
参考文献
图书序言
一场疯狂大脑的探险之旅
二○○五年十月的某天,当初秋最后一丝闷热从南加州渐渐褪去,我正在对将要交付《俄亥俄刑法杂志》(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发表的论文做最后几处修改。长期以来,我对心理变态杀人犯脑部扫描图像的研究时断时续,前后跨越了十个年头,最终集结成《年轻心理变态的神经解剖学基础》(Neuroanatomical Background to Understanding the Brain of a Young Psychopath)一文。文中记录着一些你能想像到的最坏的人——他们经年累月犯下滔滔罪行。如果我可以撇开那些保密条例,向你陈述这些罪行,这些故事一定会让你毛骨悚然。
但是劣迹斑斑的过去,并不是让杀人犯有别于常人的唯一理由。作为一个年过而立的神经学家,数年来,我看过了无数的脑部扫描图,杀人犯们的图像却与众不同。他们的脑部扫描图都呈现出一种罕有而令人担忧的共同特征,即额叶(frontal lobe)和颞叶(temporal lobe)(通常来说,这两部分与自我控制密切相关)脑功能低下。这些部位的活跃程度低下,暗示着患者缺乏道德推理和抑制自身冲动的正常能力,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些罪犯都拥有不人道的暴力犯罪记录。我在论文里说明了这些特征,交稿后便投入到其他项目中去了。
进行杀人犯脑部扫描图研究的同时,我的实验室还在进行一项基因方面的独立研究,想要找出与阿兹海默症有关的特定基因。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我和同事们为一些阿兹海默症患者做了基因测试和脑部扫描,同时也为我的家人做了相同的测试,作为实验中的正常对照组使用。
十月的那一天,我正坐下来分析家人的脑部扫描图,那叠图片里的最后一张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看起来非常奇怪。事实上,这张扫描图看起来正像是我在论文里提到的那些不正常图像,也就是说,这张图像的主人是个心理变态—或者说,至少与心理变态者同样有着某些让人不愉快的特质。我对家人并没有这方面的怀疑,所以自然而然地认为是家人的扫描图中混进了别的图像。
通常,在同时进行几项研究的情况下,即使我竭力让所有工作井然有序,但东西放错地方这类事情也是在所难免的。麻烦的是,为了将所有的扫描图做匿名处理,我们将所有图片随机编码,并且隐去了图片主人的姓名。所以为了确保我没有弄错,我让实验室的技术人员撕开了编码。
看到了图像主人的名字之后,我觉得这当中出了错,便气急败坏地命令技术员们去核对扫描器,检查其他技术人员们做的图像和资料库。但一切都毫无差错。那确实是我的脑部扫描图。
来想像一下这样的场景:
这是一个週六的早晨,天气晴朗温和,你决定要去家附近的公园散个步。信步游园之后,你在树荫下的长凳坐下来歇息,旁边还坐着一个长得不错的年轻人。你们互相问好,他也附和说:「天气真不错,活着真好。」接着你们又交谈了十五分钟,对彼此产生了大致的印象。在这短短的十五分钟里,你们可以了解有关对方的很多事情,也许你会知道他谋生的职业,他是否结婚了,有没有小孩,又有些什么业余爱好;也许他看上去聪明、迷人、坦率、有趣,还会讲很多有趣的梗,总的来说,和他的谈话令人愉快。
基于你谈话的对象,接下去的十五分钟可以出人意料地告诉你更多。比如,如果他是个早期的阿兹海默症患者,他可能会开始重复刚刚说过的那个梗,重复同样的面部表情,配合同样的肢体动作,讲同一句俏皮话。如果他是思觉失调症患者,他可能会开始调整坐姿,说话的时候靠你太近,直到你觉得不舒服,起身离开,并时不时回头看看这个人有没有跟上来。
如果长凳上,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是我,你应该会觉得我大体上算是个有趣的家伙。如果你问我是做哪一行的,我会告诉你我是研究大脑的。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我会告诉你,我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医学院的一名教授。我会向你描述我的职业生涯,怎样教医学院学生、住院医生和研究生们了解人类的大脑。如果你听得津津有味,我还会跟你讲讲我那些关于成人干细胞(adult stem cells)、帕金森氏症动物病例和慢性中风的研究。此外,以这些实验室研究成果为基础,我还成立了三间生物技术公司,其中一家公司在过去二十五年里一直保持获利,另一家从同类企业中脱颖而出,不久之前被授予了国家奖。
如果你还有兴趣听下去,也许我会提到自己是很多学会和专家小组的成员,关注艺术、建筑、音乐、教育和医学研究等领域。除此之外,我还是美国国防部的顾问,致力于研究战争对大脑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你不休地追问下去,我会提到参与过的电视剧和电影,还有以前做过的各种各样工作,从酒保、工人到老师和木匠。直到现在我还留存了一张过期的卡车司机公会卡,我以前还当过卡车司机。
某一刻起,你可能会开始想,我是在胡说八道,是在吹牛。特别是当我宣称,我十四岁那年被评选为纽约阿尔巴尼教区年度最佳天主教男孩(Catholic Boy of the Year for the diocese of Albany, New York),还曾经是体育高中和大学的运动员。不过,即使你可能觉得我话太多,认为我是个满口胡言的家伙,你仍然会发现,和你说话的时候,我一直注视着你,仔细听你讲的每一句话。实际上,你可能会有些惊讶,我对你的生活是如此好奇,对你的观念和你对世界的看法也很在意。
如果你答应下次可以再见面,最后我们可能会成为朋友。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我身上一些让你不快的事——你可能时不时会发现我在说谎,或者我经常会在赴约时迟到,让你不开心。
但是,撇开我的轻度自恋和间歇爆发的自私行为,我们共度的时光还是很快乐的。毕竟,总的来说,我还是一个靠得住的好人。
一切都很完美,除了一件事,我是个边缘的心理变态。
我愿意写下这个故事,写下这个可能算不上绝对完整却绝对真实的故事,来与家人、朋友和同事们分享我整个家族的生物学和心理学背景。当然了,整个叙述都建立在来自脑造影、遗传学和精神病学的大量研究资料上。除此之外,还来自残忍的自我剖析,来自那些时不时令我不安的坦白,以及对自己和家庭的讨论分析(但愿我的家人不会在读完此书后跟我断绝关系)。
我完成这本书的目的不只是要讲故事,或是拥护什么全新的科学发现,我的愿望是能透过叙述,釐清对于一个议题的讨论,一个在我们文化中,虽然备受大众关注,却缺乏理解和共识的议题:心理变态(psychopathy)。
除了书中提到的基础科学理论和我自己的故事之外,我希望完成的研究和提出的理论可以派上用场。我希望这个关于大脑、基因和早期成长环境将会如何影响人们成为心理变态的理论,不仅可以帮助读者们,还可以在家庭教育和刑法制定这些更广大的层面中做些贡献。
也许听上去有些夸夸其谈,但是在接下来的书里谈到的理论,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完成世界和平的理想。
我提出了一个这样的假说:在那些长期饱受暴力困扰的地区,例如以色列加萨走廊(Gaza)和洛杉矶东部地区之类的地方,女性为了受到保护,会与暴力分子结合,使得拥有心理变态潜质的基因在人口中的密度增加,好战的基因得以传播开来,而这又加重了地区的暴力问题,周而复始成为恶性循环。经年累月之后,就构成了一个充斥好战分子的社会。这个假说仅仅是一个推测,却值得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下去。
我是一个坚定的科学家,一个专注于大脑神经解剖学的神经学家,这个身分也塑造了我看待自己整个成年生活所有行为、动机和道德的方式。在我看来,人类是一种机器,一种自己都无法彻底理解的机器。数十年来我也一直坚信,人类对自己是谁和自己的行为几乎无法掌控。我们的先天因素(基因)决定了个性的百分之八十,而后天因素(成长环境)只掌控其余的百分之二十。
一直以来,我就是这样看待大脑和行为,但这个观念却在二○○五年受到了与其说是激烈的,不如说是让我难堪的动摇,使我过去的观念不得不向现实不断妥协。我渐渐明白——比以往要更加透彻地明白——人类生来就是如此复杂的生物,我们不能片面看待人类的行为、动机、慾望乃至需求,任何将之简化为绝对的做法,都无益于人们对于真相的发掘。我们并非简简单单的好人或者坏人、对的人或者错的人、善良的人或者心怀恶意的人、温良的人或者危险的人。我们不只是基因的产物,并且科学也只能解释人类天性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下手中这本书的原因。
推荐序
心理变态者独一无二的自白
心理变态(psychopath),或译为人格病态,是近几年犯罪心理学相当热门的话题。长久以来,心理学家即发现芸芸众生里似乎有一种特殊的人格型态,这种人自我中心、时常不理会他人的感受、做事随兴所至,动辄视社会规范如无物……;而更重要的是,这类人似乎很难被众所周知的行为改变技术——赏与罚所改变,而且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他们自有一套心理运作的方式,使这类人始终我行我素。
自一九九九年美国爱荷华大学神经科Steven Anderson等人,在《自然》期刊发表了前额叶脑伤的幼童,在成长后行为特质如何与这类「心理变态」者相似的案例报告后,再加上大脑功能性影像学的日益发达,神经心理学家几乎肯定这类特殊的人格型态,应该就是大脑前额叶、包括杏仁核在内的某些神经回路功能特异所产生的结果。
本书作者詹姆斯.法隆也是在这个课题的学术研究方面的佼佼者,但与其他此类书籍不同的是,作者除了深入浅出地说明了相关研究的惊人发现之外,更在一次偶然状况之下,发现自己的大脑功能运作的造影结果,竟然与那些「心理变态」的个案表现极为相近。
因为这样惊人的发现,作者开始回想并反省自己从年幼到大的生活点点滴滴,从儿童青少年期的强迫症状到与同学同事之间的互动、躁郁症式的行为表现,与妻子家人之间的感情和背叛,和精神科医师的诊疗谘询,甚至追溯到自家多年前的族谱,半自传式且诚实地审视自己过去行为的模式,以及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最终赫然发现,其实自己的行为,在本质上和「心理变态」者的人格特质毫无二致。
也因为如此,这本书独一无二地透过作者的自我剖析,生动地告诉我们一个「心理变态」者如何潜藏在我们的身边,但也如何因为自幼父母、家人、成长过程中诸多朋友的帮助,成长为一个基本上对社会无害,且相当有成就的科学家。
本书译文流畅,对于学术专有名词及学理的理解掌握精准,是难得一见的科普翻译佳作,相当值得细读。
彰基司法精神医学中心主任 王俸钢
推荐序
爱让人不会成为魔鬼
关于推荐这本书之前,我想到了倪匡所写过的一本小说《创造》。在这本小说里,有个抢劫犯被科学家当作实验品,希望可以用科学家的脑为模范,来改造这个犯人的脑部,让这个犯人以后可以循规蹈矩。结局是,科学家夫妇在帮这个罪犯进行手术后被罪犯杀害。主角卫斯理本来以为是改造失败,后来发现其实改造成功了。因为,会想改造别人思想的人,本身就是罪犯。用罪犯的脑部当范本,改造好的人,仍然是罪犯。
幸好,本书的作者法隆(James Fallon)并没有这样的企图心。当他发现自己的大脑图像跟心理变态者相同,而过去家族四百年来又充斥着犯罪的历史时,他心里觉得非常恐慌。于是他写下了这本书,以他自己的成长经验与家族史为分析标的,并且搭配科学关于基因、干细胞、中枢神经等的生动描绘,探讨是否有「天生变态」这件事。
法隆跨出这一步是很勇敢的,因为他必须揭露自己与家族过去的疮疤,诚实地面对自己经常需要压抑的慾望。他希望透过自身的经验与学理告诉阅读者这句话:「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可以选择的。」他认为,适当的家庭环境与爱,纵然不能完全地驱逐与心理变态相关的特质与基因,但是却可以透过更多的关注,让某些人至少可以不会变成魔鬼。
用心理变态这个形容词来描述罪犯,或许不是很适当。毕竟有许多的所谓罪犯,如果按照法隆的说法,就是无法压抑自己内心的冲动而犯罪,但是这样的冲动或许其实是充斥在许多人之中的,只是有做与没做的差别而已。也因此,从这本书当中,或许我们不需要把犯罪当作是基因与必然,而是可以进一步深思,如果人性真的本恶,我们应该如何让本恶的情况约束在法律、情感与道德的框架下,让损害不至于扩大,甚至可以帮助别人。
法隆的用意,应该不是在强调犯罪命定说,而是想要告诉把命运归咎给基因的人,可以选择、可以改变,透过适当的方式,人都可以更好。最后,让自己透过贡献社会,得到更多的快乐。
律师 吕秋远
推荐序
心与脑的双重自剖
回顾个人心理发展历程,而做出自传式剖析的文章还不少;拿自己做实验,接受脑部摄影检查并自我判读的科学家也有一些;但能就心理特质与脑部影像进行双重自剖,然后写成专书的,大概就只有詹姆斯•法隆了。
原本只是把自己当成对照组之一,参与一项阿兹海默症的脑部摄影研究,当片子交到他手上时,长期研究重刑犯脑部的他不禁惊唿:「怎么跟那些恶贯满盈的心理病态者(psychopath)的脑部特征这么相像!」但他明明是一个声望卓着的脑神经科学家,没有任何犯罪纪录,怎么会有这样的脑部结构?于是他展开了成长历程的自我探索,也请教了诸多亲友与心理学家对他的看法,试图从心理与脑部两端分头进行,来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最后他将这样的探索历程写成了《天生病态》这本书。
詹姆斯‧法隆是美国加州大学的脑神经科学教授,他长期研究冷血杀手的脑部影像与犯罪行为的关联,因此由他来讲述心理病态者的脑部特征与心理特质,可说娓娓道来,深入浅出,不管是门外汉或犯罪学家翻开此书,都能获得阅读的趣味与智识的成长。
然而詹姆斯‧法隆写这本书的企图心不只如此,他更借由心与脑的双重自剖,想要探触底下这个重要课题:到底天生穷凶极恶的心理变态者,有没有可能长成一个奉公守法的好人?抑或他们是坏胚子,坏到脑组织里去了,不可能透过后天环境的力量扭转天性?
台湾最着名的心理病态者应该是白晓燕案兇手陈进兴,他符合本书所提四大心理特质:冲动、浮夸、欠缺同理心与反社会倾向。但陈进兴没有接受脑部摄影,无从得知是否具有前额叶与杏仁核等部位的脑部缺损特征,也不知他是否带有所谓的「战士基因」MAO-A,而天生喜欢逞凶斗狠。基本上台湾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近两年最残暴的杀手,台北捷运随机杀人兇手郑捷,是不是心理病态者?如果是,能不能在他小时候透过心与脑的检查预先得知,然后借由家庭、学校与社会的正向力量,比如持续够多的关怀、教育与导正,让他的攻击倾向留在基因与脑部,永远不表现出来?
遗憾的是,台湾社会连想要理解郑捷的企图都没有,只会急着将他枪决,以求大快人心。形成此一氛围的因素之一,多少乃因对于重刑犯犯罪心理与脑神经科学的漠视。《天生病态》这本书正好可以给台湾社会一个刺激,让众人一起思索:那些重刑犯是否天生冷血?除了坐等他们犯下令人发指的杀人案以外,这个社会还可以做些什么?
推荐序
命定与命运的对抗
唸科学的人通常不迷信,我们相信机率、接受巧合,但不接受命定。但是本书的作者和另外一本《暴力犯罪的大脑档案》(The Anatomy of Violence)的作者Adrian Raine,两人大脑的扫瞄图居然都跟犯罪的人很相似,两人又都是名校的教授:Raine是费城宾州大学的讲座教授,本书作者是加州大学尔湾医学院的教授,这个巧合未免太高了,正因为两人都是学术界的名教授,两人的大脑又都显示反社会行为,这就更使人想从他们身上去寻找犯罪的因素,为什么他们可以在社会中正常生活,不会去为非作歹?
人的行为受大脑的控制,而大脑又会因行为而改变。也就是说,大脑是基因和环境互动的产物。过去的基因决定论是错的,科学证据显示人的大脑会随着环境的需求而改变以求生存,例如动物会制造维他命C,人体本来也会,但是到一万年前,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可以从外界稳定地得到维他命C之后,这个能力便退化掉了。当然,那时没有办法看到人会有远洋航行,三个月不靠陆,船员会得坏血病,牙龈流血。
因为环境会塑造大脑,所以后天的经验就很重要。贫民窟的精神官能症比较多,因为环境会促发或抑制基因的展现。作者有家族的暴力犯罪历史,又有暴力基因(单胺氧化酶Monoamine Oxidase A, MAO-A较少),但是他有个正常的童年,所以他没有走上犯罪之路。
童年的遭遇是影响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因素,就像作者说的,一、二岁时的受虐后果比五、六岁时受虐大,而五、六岁时的受虐后果又比十二、三岁时大。大脑,尤其前额叶皮质(Prefrontal Cortex)的正常发展对孩子行为的控制来说太重要了,这也是我在接到本书的书稿,知道只有不到一週的时间写书评时,还是愿意放下手边的事先来做的原因。太多父母以为孩子小、不懂事,在孩子面前作坏事,这些经验都铭印到孩子大脑中,影响他的一生。我迫切希望父母在阅读本书后,能了解后天环境对孩子大脑的影响。
其实,在看书稿时,「反社会人格」这个名词一直在我脑海中出现,作者有着不折不扣的反社会人格,外加强迫症、躁郁症……,他的大脑影像图的确是不正常的,非常像我们在骗子(con man)大脑中看到的那样。但是他没有进入监狱,因为他的家庭正常,并有很深的宗教信仰(母亲是西西里的天主教徒),他虽然不在乎伤害别人,却没有刻意去伤害别人的意愿,所以没事。
人不能选择父母,也就不能选择基因,但人可以打造环境,使不好的基因不展现,人的命运还是在自己手上的。
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 洪兰
图书试读
一张脑部扫描图引起的混乱
一个心理变态可以伪装出很关心他人或是充满悔意的样子,但他的大脑却会说实话。
这就是我在二○○五年那个十月一直在做的事,直到我发现了自己怪异的脑部扫描图,暗示我的大脑在负责同理心和道德的部分活动减弱。
「心理变态是什么?」
身为一个科学家,在看过自己的大脑扫描图像之后,我开始从更专业的角度,而非出于个人的惶恐来思考这个问题。我开始询问心理学同事们,想知道自己是否与心理变态这个身分相符。我谘询了一些业内最杰出的研究人员,却没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有些人回避这个问题,说心理变态根本不存在。要定义一个心理变态就像是要定义精神崩溃那样让他们无从下手。「心理变态」这个词已经被大众用惯了,但从科学和专业的角度却难以定义(就像「蔬菜」,这个在厨房里被惯用的词,却不是生物学上的用词)。
撇开「心理变态是否确实是一种心理障碍,如果是,那它的定义又是什么」这个议题不论,医学界针对心理变态已经有一些被广泛接受的量表。其中最着名也是最为广泛使用的测试量表是PCL-R(Psychopathy Checklist- Revised,心理变态测评量表修订版),也因为它的设计者,加拿大的罗伯特.海尔(Robert Hare)医生而被称为「海尔量表」(Hare’s Checklist)。海尔量表包含十二个测试项目,每个项目都分为0、1、2三个评分,以评价患者心理变态特征的三个等级:无症状(0分),部分符合该症状(1分),完全符合该症状(2分)。
在这个标准下,一个获得「满分」40分的人,就可以被视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心理变态者。通常来说,超过30分即可被诊断为心理变态;有时候,测量结果超过25分也会被诊断为心理变态。测试会由一名经过专业训练的医师负责评分,一般是以晤谈形式,由临床医生访问受评估者,有时医生会得到受评估者的犯罪记录、医疗记录及第三人的观点作为参考。对受访者的评估,也可以在受评估者缺席的情况下完成。
所有的心理变态特质可以被归为四类,或者说是四种「因素」,如下:
人际因素:包括肤浅(只做表面功夫)、表现夸张、充满欺诈。
情绪因素:包括缺乏悔意、缺乏同理心、拒绝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行为因素:包括行事冲动、缺乏目标、为人不可靠。
反社会因素:包括暴躁易被触怒、有青少年违法或犯罪记录。
用户评价
老实说,《天生变态:一个拥有变态大脑的天才科学家》这个书名,绝对是我近期读过的最“吸睛”的了。我之前也读过不少关于科学家的传记,但很多都倾向于描绘他们如何理性、如何严谨,有时候会觉得少了那么点“人味”。这本书的书名却直接点出了“变态”,这让我感觉作者在尝试一种更直接、更具冲击力的方式来探讨天才的本质。我猜想,这本书可能不会拘泥于枯燥的理论推导,而是会用一种更故事化的方式,展现这位科学家是如何“变态”地思考,又是如何把这些“变态”的想法付诸实践的。我很好奇,这种“变态”的大脑,会不会让他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模式,或者对事物产生独特的联结?会不会在他的研究过程中,有一些“非线性”的跳跃式思维,让其他科学家匪夷所思,但他最终却能因此获得突破?我希望这本书能描绘出,这种“不按牌理出牌”的思维方式,是如何在科学的严谨框架下,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它可能会让我们重新思考,究竟是什么造就了真正的科学巨匠,是循规蹈矩,还是勇于颠覆?
评分当我在书店看到《天生变态:一个拥有变态大脑的天才科学家》这本书时,它的标题让我停下了脚步。我觉得,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能够抓住读者眼球的书名非常重要,而这本书无疑做到了。我对“变态大脑”这个说法很好奇,它究竟是指代一种超乎常人的智力,还是一种不按常理出牌的思维模式?我推测,这本书可能在探索天才成长的心理历程,尤其是在他们与“正常”社会产生差异时所面临的挑战。我很好奇,这位科学家是否在童年时期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是否在求学过程中经历过不被理解的孤单?书中会不会描绘他如何在高压和质疑下,保持对科学的热情和专注?我尤其希望,这本书能够深入探讨“变态”的另一面——那就是创新和突破的可能性。它是否会告诉我们,正是那些看似“离经叛道”的想法,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我期待这本书能带来一种全新的视角,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些在各自领域内“特立独行”的杰出人士,并从中获得启发,勇于发掘和拥抱自己内心的“不一样”。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真的很大胆,一看到《天生变态:一个拥有变态大脑的天才科学家》,就忍不住好奇起来。不过,坦白说,光看书名,我会有一点犹豫,毕竟“变态”这个词通常带有点负面的联想。但“天才科学家”又让人眼睛一亮,这种强烈的反差感,反而激发了我对这本书内容的浓厚兴趣。我很好奇,作者到底想通过这个书名传达什么?是探讨天才与常人思维的差异,还是揭示那些不被理解的创新者内心深处的挣扎?也许,所谓的“变态”并非贬义,而是一种突破常规、超越自我的独特视角。我猜想,书里可能会描绘一个不被世俗所理解,甚至被误解的天才,但他却凭借着异于常人的思维方式,在科学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种“孤注一掷”的创新精神,以及随之而来的孤独感和坚持,是我特别想在书中看到的。它会不会是一部关于打破框架、挑战权威的作品?会不会让我们重新审视“正常”与“异常”的定义?我非常期待能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也希望它能带来一些启发,让我们在看待那些与众不同的人时,多一份理解和包容。
评分《天生变态:一个拥有变态大脑的天才科学家》这个书名,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话题制造机”。它直白到有点令人不安,但同时也极具吸引力,让我想立刻拿起它一探究竟。我猜想,这本书不会是那种一本正经地讲科学定理的学术专著,它更有可能是一部关于“人”的探索。我会好奇,这位科学家究竟是如何“变态”的?是他的性格使然,还是他独特的学习方式?他在生活中会不会有很多奇特的习惯,或者对某些事物有着近乎痴迷的执着?我特别期待,书中能够描绘他如何将这种“变态”的思维,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不是他在面对科学难题时,总能找到别人意想不到的切入点,或者构建出别人闻所未闻的理论模型?我希望这本书能展现出,天才的思维并非总是流畅无阻,它可能充满了矛盾、挣扎,甚至与世俗的格格不入,但正是这种“不完美”的特质,才成就了伟大的创造。它或许能提醒我们,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有时需要拥抱内心的“不羁”,并敢于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即便看起来“变态”的道路。
评分我拿到《天生变态:一个拥有变态大脑的天才科学家》这本书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它的封面设计。虽然我在这里不便描述具体的封面细节,但它的视觉呈现绝对是吸引人的。它不像一般科学读物那样严肃刻板,反而带着一丝艺术气息,也可能是一种略带叛逆的风格。这种包装,我觉得很符合书名所传递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我开始思考,一个拥有“变态大脑”的科学家,他的生活会是怎样的?会不会有许多有趣的、意想不到的日常片段?比如,他对生活中的小事有着超乎寻常的观察力,或是用科学的逻辑去解读一些看似日常的情感问题。我尤其好奇,他的“变态”思维是如何在科研中发挥作用的。是不是在别人看来毫无可能的研究方向,在他那里却是一条通往突破的捷径?书中是否会穿插一些他早期探索未知、屡屡碰壁,但又不放弃的经历?我希望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科学成就的堆砌,更能深入挖掘这位科学家在成长过程中,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如何面对外界的质疑,以及他内心深处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我期待它能带给我一种“看见”的感觉,看见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变态”天才。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权所有





![动脑玩,玩脑动[升级版]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tbooks.qciss.net/0010743539/main.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