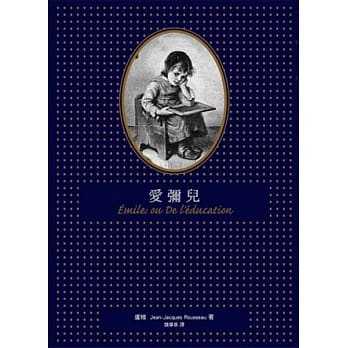具体描述
本期有三篇文章讨论卢梭政治思想在中国与日本的早期诠释与受继。此三文各有所长,但都集中于讨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Du Contrat Social),尤其是其中最具魅惑力与争议的概念:普遍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
王晓苓〈卢梭「普遍意志」概念在中国的引介及其历史作用〉是一篇分析精细且具历史纵深的精采论文。王文认为,十九世纪末日本人中江兆民精到的汉文译本《民约通义》开启了中文世界对卢梭政治思想的关注与讨论。循此,王文约略依清末、民国、1949至文革、1990年代后等四个时期,分别列举、阐述几位具代表性人物。论文的前大半部依序讨论梁启超与汪精卫,严复、章士钊、张奚若,何兆武,王元化等人对「普遍意志」的理解与争论;是精细的文本分析。
王文认为,卢梭的政治思想,尤其是「普遍意志」概念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彰显人不可让渡的自然主权—因此可能主张激进民主;另一方面,它又强调政治社会中的成员,也就是公民必须服从普遍意志的指挥—因此可能形成极权统治。这个两面性导致了历来中文世界对卢梭理解的分歧。王文最后从时代背景、政治议程以及政治环境的变迁等外部因素,论证上述各家对于卢梭思想理解的差异。从君主立宪到革命,从相信进步的人民民主到反左,在不同的政治光谱下,反射出卢梭的不同样貌。总之,王文是篇黑格尔式的思想史论文,以后世、历史后设的立场,逐一审视主要阐述者的理解、翻译、衍伸及其阐述的时代背景。在一种「全知」的眼光下,希望对过往的诠释文本投以时代性的理解。
范广欣的〈卢梭「 革命观」之东传:中江兆民汉译《民约论》及其上海重印本的解读〉是问题意识清晰,论理强势的学术文章。范文认为,卢梭政治思想并不强调革命,并不鼓吹消灭君主统治。那么,范文问道:「近代以来中国人是怎样通过阅读《社会契约论》发现了革命呢?」这问题等于暗示、追问了中国近代革命意识的起源。根据范文的理解,此间与中江兆民翻译《社会契约论》,也就是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的《民约译解》密切相关。范文大量利用中江兆民自己在译本中所加入的个人意见-〈解〉-,企图说服读者,中江兆民以相当迂回、夹译夹注、几近微言大义的方式, 逐渐将卢梭的「反对君主专制」,往「否定君主制本身」推进。范文进一步论证,中江刻意使用「党」一字来表示‘society, aggregation, association, community, union’等多种不同概念,明显带有革命党的修辞意味。相较于王文的历史纵深,范文完全集中于中江兆民文本的内外部分析,特别注意中江遣词用字的意旨。但范文也注意到《民约译解》在中国以《民约通义》重印面世时所发生的文本再造,尤其是重印版的序言,较诸中江激进,根本就是「彻底否认君主专制,而承认革命的正当性」。换言之,从日本的《民约译解》到中国的《民约通义》,中国近代的革命思想依着这份亚洲的卢梭文本而生长。
萧高彦〈《民约论》在中国:一个比较思想史的考察〉是篇方法论意识极为清晰的论文。上述范文的论述重作者认定的正确的、非革命的卢梭,对照中江文本不狃于时而造作出的潜在的革命话语,以及此话语在晚清中国情境下的放大。如果范文可看成史特劳斯式的(Straussian)的文本解读,萧文则是自承、自省的史金纳式(Skinnerian)思想史书写:以翻译文化理论来平衡史金纳方法论中的主体意识与作为,而凸显在地文化条件所酿酝的新种政治语言。萧文的分析对象以中江兆民、杨廷栋、刘师培、马君武为主,说明这些译者及其文化在特定条件下所构思的翻译策略与概念传递,创造出甚么政治想像。以中江为例,他「君」「邦」「民」「士」「臣」等词分别代表sovereign, power, people, citizen, subject等等,显然是以儒家政论来安置新的、未来的政治秩序想像。但萧文的目的不止于观念的比较,而进一步指陈,这些特殊的翻译可能指向何种政治议程。中江兆民以「君权」翻译sovereign,少了「主权者」这抽象的概念,导致了「以人民自为君主」遮蔽掉了「以人民自为主权」。其结果,传统的个人君主统治制度在《民约论》里变成不可能的选项。这其实反倒相当唿应中江在译着里强调的「民约」主轴。萧文最精采的分析应该是有关杨廷栋的部分。从上述王文或范文的角度看,杨廷栋的翻译显得粗糙且错漏百出。但萧文以文化交会暨脉络化方式来理解杨廷栋,反倒得出令人惊喜的文本诠释。萧文认为,关键在于杨廷栋以「公理」来翻译「普遍意志」。这固然使得卢梭文本可以与传统儒家清议概念疏通,但更重要的是,它「将卢梭的『民约』」「转化成一种宪政主义论述」。这显然也与杨廷栋强调舆论、议会或「集言之制」互为表里。用更简洁的说法就是,杨廷栋将卢梭洛克化了。而到了刘师培、马君武等革命派,他们则强调危急时刻的「特别会议」,普遍的平等观念,以及人民的权力等等指向在清末政治情境下的革命正当性话语。尤其是马君武以「帝权」来指涉人民主权,显然「超越了中江的语汇系统」。上述三篇文章分进合击,将以「民约」、人民主权等概念为主的中国近现代政治语汇,甚至文化传递的研究做了具有多重对话效果的精致展示。无论后继研究者对这些论文评价为何,任何超越企图,都必然具相当挑战性。
林正珍的〈分裂的亚洲认同:近现代东亚世界观的对位式呈现〉主题与前述三文相当不同,文类风格也完全迥异,但所论时代与社会则高度重叠,对研究近现代文化思想者,这四篇论文之间应该有相互印证启发之用。林文提示道,相较于中国天下观的限制,亚洲的亚洲概念是日本文化特殊论的产物。此概念一方面显示出日本国族在既有的,亦即西方中心、资本主义的世界史框架中,追寻主体的努力,另一方面则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理性化或合理化接榫。这是相当精确也深具启发的观察。此外,林文仔细描述了日本思想界如何在近六十年从新亚细亚主义,也就是自任融合东西文明的角色,逐渐转向多元与自省的亚洲观。此一宏观的历史态度之考察,应该可以提供中日近现代比较史或交流史的研究者一个思考背景。
多元思考同样是戴丽娟〈法国史家的记忆课题:近三十年的重要着作与讨论〉一文的重要元素。戴文详细介绍法国史家对于何谓历史记忆所进行的发明、写作与反省。根据戴文,历史记忆就是相对于学院历史书写的历史。它是民间的、多样的、地方的、分散的,甚至是个人的。换言之,我们现今所怀抱的性别、阶级、国族等等认同,很可能有相当程度,来自非学院历史的建构。这个认定或观察,就是历史记忆研究的起点与主要内容。这既是学院历史的反省,也是学院对非学院书写的介入。但是,诚如戴文所精确交代的,此一学院历史的反省与介入—「记忆之所在」,也可能成为非学院、民间、或媒体所欲收编的「所在」。本文是中文世界少见有关此一主题的详尽介绍,相信它对中文世界西方现代史学史相关研究应该会有长久影响。
著者信息
王晓苓
1959年生于中国山西太原,西安外国语大学法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巴黎七大东亚语文学院博士。2009-2011年,巴黎狄德罗大学东亚学院(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 -Paris 7)中文系主任,现任巴黎狄德罗大学东亚学院助理教授,美非亚社会科学研究中心(CESSMA)成员,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以及卢梭对中国的影响。主要着作有:Qu Qiubai(1899-1935)« Des mots de trop » - L’autobiographie d’un intellectuel engagé chinois, Editions Peeters Paris-Louvain, 2005(《瞿秋白〈多余的话〉:一个中国知识份子的自传》与鲁林Alain Roux合着); Jean-Jacques Rousseau en Chine : de 1870 à nos jours, dans l’Edition Musée Jean-Jacques Rousseau–Montmorency,2010(《卢梭在中国:1870年至今》,法国蒙莫朗西卢梭博物馆出版);以及多篇关于卢梭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引介及评论的论文。
范广欣
江苏扬州人。香港浸会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助理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学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硕士、博士,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博士,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哲学以及比较政治理论,论题包括晚清读书人对中国经典传统的重新诠释、革命与民主理论、社会契约论和激进思潮及其传播与解读。曾发表〈从民本到民主:罗泽南、中江兆民和卢梭论反暴君〉、〈「怀柔远人」的另一解释传统〉等十余篇论文。
萧高彦
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目前借调科技部担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司司长。研究专长为西洋政治哲学、当代政治理论。
林正珍
现任中兴大学历史系教授、台湾叙事学学会理事长。研究领域:史学理论、叙事学、中国近代思想史。着有《近代日本的国族叙事: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台中乐成宫旱溪妈祖遶境十八庄》专书及相关学术论文多篇。
戴丽娟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学博士 现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
专长为十九、二十世纪法国史
杨正显
台湾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学术思想史、阳明学与辑佚学等。主要着作有《一心运时务:正德时期(1506-21)的王阳明》、〈王阳明《年谱》与从祀孔庙之研究〉、〈王阳明诗文辑佚与考释〉、〈王阳明佚诗文辑释—附徐爱、钱德洪诗文辑录〉等。
图书目录
【编辑语】
【论着】
王晓苓 卢梭「普遍意志」概念在中国的引介及其历史作用
范广欣 卢梭「革命观」之东传:中江兆民汉译《民约论》及其上海重印本的解读
萧高彦 《民约论》在中国:一个比较思想史的考察
林正珍 分裂的亚洲认同:近现代东亚世界观的对位式呈现
【研究讨论】
戴丽娟 法国史家的记忆课题──近三十年的重要着作与讨论
【书评】
杨正显 评方祖猷《黄宗羲长传》
图书序言
图书试读
「普遍意志」是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核心概念。由于其内涵极其复杂,并具个人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双重趋向,历来对其意涵的解读众说不一,论争不断;其争议性也影响到卢梭思想在中国的解读。通过考察最初的两个《社约论》汉译本,以及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不同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相关论着,本文试图以对照分析的方法,来探讨这一概念是如何翻译和解读的,以及每个时期对这一概念不同解读的历史根源。
其实,卢梭「普遍意志」概念在中国所引发的不同诠释以及争议,往往与不同时期的国情紧密相连。耐人寻味的是,辛亥革命前以及民国时期对卢梭「普遍意志」的批评主要来自对「国民」资格的怀疑,担心天赋人权说会使人人滥用自由,最终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
显然,把卢梭学说视为倡导个人极端自由之说。解放后,卢梭的政治理论被视为「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理论而被边缘化。而文革之后,卢梭的「公意」理念被诠释为「消融了特殊性与个体性」的抽象普遍性,成为导致「极权专制」 的理论依据。如今,卢梭成为学术界研讨的对象,回归作者原着,按照思想家本人的逻辑来挖掘和解读卢梭思想的原始意涵成为当今学者的研究方向。
通观卢梭的政治论着,我们以为卢梭试图通过「普遍意志」原则来构建一种使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之间和谐的政治体制。因此卢梭所反对的不是每个人的私利,而是有损于平等自由的个别意志或特殊利益。探讨这一理念的深层内涵及其在中国的接受历史,对当下仍具现实意义。
范广欣 卢梭“革命观”之东传:中江兆民汉译《民约论》及其上海重印本的解读
本文通过中江兆民汉译卢梭《民约论》及其译本在清末上海的重印,讨论欧洲政治理论如何进入东亚知识份子的视野,并推动他们的思考和行动。
用户评价
這是一本在學術深度和閱讀趣味之間取得了極佳平衡的著作。作者並非簡單地將盧梭的思想與中國的早期共和實踐進行「照搬」式的對比,而是展開了一種更為辯證和富有層次的研究。他首先對盧梭在《論不平等的起源》、《社會契約論》等經典作品中的核心觀點進行了清晰且系統的闡釋,深入剖析了盧梭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判斷,以及他對政府權力來源、人民主權原則、公意如何運作等問題的獨到見解。這些理論性的梳理,為後續的討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後,作者巧妙地將目光投向了中國的近代,特別是那些試圖擺脫帝制、探索共和道路的知識分子和政治運動。我驚訝地發現,原來在翻譯和引入盧梭思想的過程中,中國的思想家們所面臨的文化隔閡、概念轉換的困難,以及他們如何試圖將這些外來思想與中國本土的政治傳統、社會現實相結合,都展現了思想傳播的複雜性。作者不僅關注了顯性的影響,更挖掘了隱性的呼應和變異,讓讀者在理解中國早期共和思想的同時,也對盧梭思想的傳播路徑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
评分作為一個熱愛歷史和哲學的讀者,我一直認為,理解一個時代的思想,就必須將其置於當時的社會歷史情境中。這本《思想史3:盧梭與早期中國共和》恰恰做到了這一點,而且做得非常出色。作者對盧梭思想的剖析,不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更深入探討了這些思想是如何影響了法國大革命,又是如何在後來的歐陸思想版圖中激起波瀾。而當他將視角轉向中國時,更是將盧梭的某些關鍵概念,如「人民」、「主權」、「意志」等,放在了晚清民初那個風雨飄搖、尋求國家重生的關鍵時期,與中國的知識精英們的討論進行了對照。我看到,即使是中國的維新派、革命黨人,他們在提出各種政治改革方案時,雖然使用的語言可能和盧梭不盡相同,但其背後所蘊含的對於人民權利、國家正當性來源的探問,以及對傳統專制體制的批判,都與盧梭的某些思想遙相呼應。作者通過精細的文本分析和歷史考證,展現了這種跨文化、跨時代的思想交流與碰撞,讓「共和」這個概念在中國的早期實踐,變得更加豐富和立體,也更加凸顯了思想的生命力。
评分這是一本充滿「對話」精神的書。它不是單純地介紹盧梭,也不是簡單地羅列中國早期共和思想的史實,而是將兩者放在一個更廣闊的視角下,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思想對話。作者對於盧梭思想的梳理,極為扎實且深入,從他的自然狀態論,到對私有財產的批判,再到他對代議制民主的疑慮,都有著精闢的分析。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並沒有將盧梭的理論視為一個完美的、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而是呈現了其思想中的複雜性、矛盾性,甚至是可以引發爭議的部分。接著,他將目光轉向中國,探討在西方思想傳入的背景下,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如何理解、誤讀、吸收,乃至於揚棄盧梭思想的。他特別關注那些在轉型時期,試圖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基礎上,建立一種新型共和模式的先驅們。透過對比,我更加理解了中國近代思想史上,那種既渴望擁抱西方進步思想,又力圖保留自身文化獨特性的複雜心態。這種「拿來主義」背後的本土化掙扎,在書中被展現得淋漓盡致,讀來引人深思。
评分這本《思想史3:盧梭與早期中國共和》真是讓我大開眼界,身為一個對思想史略有涉獵的台灣讀者,我一直覺得盧梭的思想與我們東方文化、特別是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之間,可能存在著微妙的連結,但礙於語言和學術斷層,一直無法深入探究。這次這本書恰恰填補了我的知識空白,作者以一種極為細膩且具備宏觀視角的方式,將西方啟蒙巨擘盧梭的思想精髓,與中國在經歷了漫長帝制轉型、孕育共和思想的早期階段進行了精準的對話。從盧梭對於「公意」的闡釋,對社會契約的構想,到他對個人自由與社會權力之間張力的深刻反思,作者都逐一梳理,並且巧妙地將這些概念置入中國近代史的脈絡中。我尤其欣賞作者對於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面對西方思潮時,如何曲折地吸收、轉化,甚至在原有文化土壤上加以「在地化」的描寫。那些在翻譯、詮釋盧梭思想時所展現出的困惑、掙扎與創新,透過作者的筆觸,變得栩栩如生。讀起來一點也不枯燥,反而充滿了歷史的張力和思想碰撞的火花,讓我重新思考了「共和」這個概念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樣性與共通性,也對中國早期共和思想的形成有了更為立體的理解。
评分說實話,當我看到書名裡出現「盧梭」和「早期中國共和」時,心裡其實是有點忐忑的。畢竟,這兩者看似跨越了巨大的文化鴻溝,一個是歐洲啟蒙時代的代表人物,另一個是亞洲古老國家的現代轉型。但閱讀的過程,卻徹底顛覆了我原有的預設。作者並沒有生硬地將兩者進行比較,而是透過一種「思想的回響」和「概念的變奏」來展開論述。他詳細爬梳了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等著作中的關鍵概念,比如人民主權、自然狀態、政府的權力限制等等,然後將這些概念比對中國近代知識人在探索國家走向時所提出的各種主張。我驚喜地發現,儘管表述方式和文化語境全然不同,但許多中國思想家在追求國家獨立、反抗專制、建立新型政治體系時,所關切的核心問題,竟然與盧梭所提出的問題有著奇妙的共鳴。例如,他們對「民意」的重視,對「官民關係」的反思,對「權力如何制衡」的探討,都隱約可見盧梭思想的影子,或者說是對類似困境的普遍性回應。作者的功力在於,他能細緻地辨析這些相似性背後的差異,也挖掘出那些因為文化傳統和歷史經驗不同而導致的獨特發展路徑,讓人不禁讚嘆思想的普世性與在地性的辯證關係。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权所有